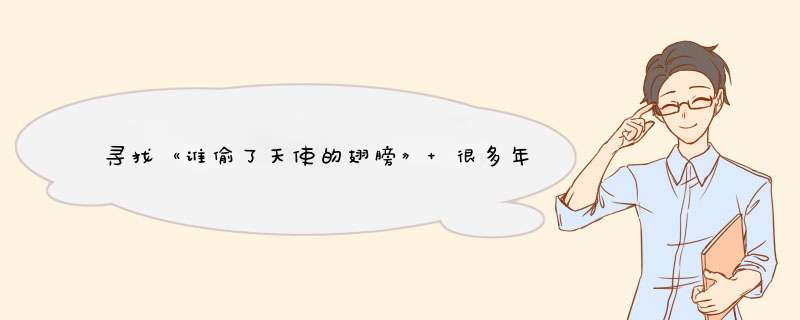
谁 偷 走 了 天 使 的 翅 膀
程 林
每个人曾经都是自由飞翔的天使,只是我们的翅膀被无数欲望的绳索缠住了。几万年以后,我们的翅膀才变成了双手,但我们还是什么都抓住不放。
作者题记
A
我一直游荡在这座城市,大概已经有十年了。我就这样背着理想的空麻袋,想找到一些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但现在我放弃了,行走成了我唯一的目的。
象往常一样,我骑着公司的助动车从虹桥跑到五角场。这条路名我不能告诉你,我有义务为我的客户保守秘密。敲开一扇暗红有些斑驳的木门,会有一位头发灰白但衣着洁净的老太走出来,接过我手里的玫瑰,然后在我的送货单上留下一个很秀气的签名,如烟。看得出老太年轻时是个美人胚子,“谢谢侬”老太柔声地说着关上门。
不能说我没有好奇心,持续一个月来,总有一位在世贸商城八楼有一间单独办公室的二十多岁的先生,让我给一位老太送玫瑰花,我偷偷的数过共有二十八朵。每次老太收到花,都面无表情,根本看不出是喜是忧。这让送花的先生多少有些失望,他几乎每天都要问我,“老太有什么反映吗?”我摇摇头,他也跟着摇摇头,叹口气,然后说:“你去吧!”
B
干上速递员这行,也是为了吃口饭。这些年,我象一只被钱逼得东躲西藏的老鼠,一直在挪窝。
阿香离开我已经一个多月了,虽然和我一起从苏北出来,我们分分合合已好多次了,但象这么久还是第一次。阿香是那种我们在**中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乡下女孩,淳朴善良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当然,带着这样的女孩子一起流浪,我变得非常危险。
半年前的一个夜晚,阿香突然哭着从金龙商厦跑到大东门。大东门是上海老城厢一个棚户区,也是苏北人比较集中的地方。羊肠似的弄堂里还保留着石头铺成的“弹格路”,有些破旧的门前总堆着一些现在不需要又舍不得扔掉的东西,让这条本来就狭小的弄堂更显得凹凸不平,如同一根双面的锈锯条,任岁月把这群人从生活的大树上锯下来,并且象木榍一样随风而散。
“当当”敲门声粗暴而急促,“谁”我大声喝道。我在上海没有几个朋友,房租也刚刚交过,谁还敢这么嚣张的砸我的门,除非是查暂住证的民警。不过,现在民警也搞满意工程,态度也称得上是“友善的狗”了。我“哗”的拉开那扇三夹板钉成的门,一个女人一下子扑进我的怀里。黑暗中,我想抬起她的脸却摸到一手的泪水,“哥,我被人欺负了。”原来是阿香,我知道出事了。
其实我早就知道会出事,不过没想到会这么快。阿香去金龙商厦做一个温州服装老板的营业员,她自己特别高兴。她常和我说:“今天营业额做了3000多元,老板奖我一件300多元的羊毛衫”
“今天营业额做了4000元,老板送我一只金戒指。”
“今天营业额做了4500元,老板给了我500元,让我去买化妆品。我才舍不得呢,我给爸妈寄了400元,自己只买了一只口红。你看漂亮吗?”说着她将鲜红的嘴唇递了过来。“很漂亮”她看得出我的应付,阿香是个聪明的女孩。她就象一颗苏北田野遗落的种子,偶然被人扔到了花盆内,并且给她阳光雨露,没多久就长成了一朵娇艳欲滴的花。城市就是这样一只花盆,我们这些苏北乡下来的种子,只要给我们一点机会,我们就能长成一棵向上的传奇。
虽然我隐约感到了危险,但男人的自尊让我无法告诉她。又过了一段时间,她终于从我这里搬出去了,说公司专门为打工的准备了集体宿舍。我要去送她,她坚持不让,我就没去。其实我本来就没想去送她
“谁欺负你了?”血一下子都涌进了我的双眼,愤怒让我浑身充满了报复的力量。我随手拎起一把工地带回来的铁板手,揣进后腰。“温州老板又和另一个营业员小浙江好上了,昨天被我堵在他家的床上。。。。。。。”后面的话我已经听不见了,我只觉得两耳呼呼生风,我向金龙商厦狂奔,看到灯火辉煌的商厦,我慢慢放缓了脚步,我不能让他们把我看成一只乡下土豹子。
我在商厦后门对面的一条弄堂里坐下来,那里有两个安徽妹在买“柴板小馄饨”,一元钱一碗,虽然皮厚肉少,但汤里放了不少猪油和辣椒粉,喝起来香辣够味。大约9点左右,温州老板和他两个朋友边说边笑的走了出来。我从没和阿香说过自己曾跟踪过她,她和温州老板的那档子事让我心疼得足有半月没睡好。我迎上去,忽然拔出铁板手狠狠地向温州老板身上砸去,他本能的抬手一挡,只听见他“哎呀”一声往后直退,他的两个朋友见状,从安徽妹个馄饨摊上操起两张长条凳向我打来,我拼命挥动着铁板手,挥动着自己的胳膊。我听到了女人的尖叫、碗摔碎的声音、脸上溅满粘糊糊的液体,我突然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阿香两只哭肿的眼睛正凝视着我,“都成红透的桃子了。”我伸手拍拍阿香的脸,阿香的泪又刷的象断了线的珍珠掉在我脸上,我试图去给她擦干净,却越擦越多,由阴有小雨变成滂沱大雨了。我脸上成了一条河,不仅有阿香的泪水,还有我的泪水。这时,我才发觉自己是多么的无力,我无力保护自己的爱情,我无力保护自己的爱人,我无力保护自己的生命。
那夜是赶到的阿香跪在那伙人面前,苦苦哀求他们,他们才留下了我的小命。
C
我躺在床上,但疼痛让我的每一个夜晚变成折磨。而阿香也不在,她总在傍晚出门,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回来,并给我带回来一袋豆浆和两只肉包。我不敢问她,从她躲闪的眼神,我知道她瞒着我在干一件不想让我知道的事情。
她不想让我知道,我就装糊涂不问。一个星期以后,她不再出去了。这天晚上,她躺在我的身边,将热乎乎的胸膛贴过来,我无法无动于衷,但我无能为力。浑身的伤痛让我们的亲热变成我在床上的挣扎。
阿香睡得很沉,轻微的鼻息呵在我的脸上,痒痒的甜酥酥的。苏北乡下的清风明月、小桥流水,还有长辫子的少女在河边捶打着衣服,家乡的情景突然象镜头一样在我的眼前闪回,原来阿香就是我的村庄。受伤后,我第一次在我的村庄怀里睡着了。
休养的一个月,是我在上海打工最开心的日子。我躺在床上,竟然拿起放下多年的笔。在乡下,我曾经发表过不少诗歌和散文,也算一个文学青年。只是漂泊的日子,让大风把我的梦吹走了。但今天断了线的风筝又回来了,我需要对生命倾诉。
当我将一个又一个的方块字填进稿纸,仿佛又回到乡下,赤着脚将绿油油的秧苗插进春天的田野,等到十月收获沉甸甸的金黄。
我日益康复,又能和阿香做爱了。我甚至写了一首诗《纵火者》————
对,我就是那个纵火者
在你的内心点燃一把春天的大火
看,你的眼睛,火焰窜出了窗棂
你在幸福的呻吟,那些隔岸观火者
狂呼救火,而你心甘情愿的燃烧
我要点燃你身体的每个角落
我要点燃你生命的每一个夜晚
我还要为你喝下那一碗烈酒
那一碗热血沸腾的青春啊
让我和你一起更猛烈的燃烧吧
让我们成为火焰的舞蹈
D
速递公司的钱真是太好赚了。发给我一辆破助动车,三天两头莫名奇妙的抛锚,我只能推着它去客户处,总免不了一顿臭骂,而且助动车的修理费和油费总是我出,每月挣的钱不少都花在车上。
腰里的BP机又响了,让我从徐家汇赶到巨鹿路《上海文学》编辑部。“谁叫速递?”一位头发灰白的老先生抬起头,“我,请过来。”清瘦的脸上一双慈祥的眼睛看着我。我觉得他很象我的父亲,心中竟然升腾起一种想和他交往的冲动。
几天后的下午,我又来到巨鹿路作协门前,传达室的老头警惕的盯着我,不等他开口我抢先说道:“吴斯人先生叫速递。”我是从速递客户单上知道他的名字的。“噢,上去吧,他在504室。”老头微笑着一指右边的门。
我的到来,让吴先生吃了一惊。当我从那只被风雨吹打得有些破烂的包中,掏出一叠诗稿时,吴先生什么都明白了。
吴先生不仅当场看完了我的诗稿,足有21首长短句,吴先生挑了5首留了下来,其余的提了一些修改意见,让我带回去。看着天快黑了,吴先生带我去了一家面馆。一碗热乎乎的面条下肚,我的胆子也大了,口无遮拦的说了起来。吴先生静静的听着,不时的点头,然后掏出一张名片,在背面写下一个电话号码,“这是我家的电话,有什么困难来找我。”
目送着吴老先生上了公交车,我忽然觉得今晚的路灯特别温柔,象故乡的月光一样,让我有一种走在家乡田间小道上的舒适自得。也许就是在那个晚上,我才明白上海是一个海,她能容纳每一条奔向她的河流,她能容纳投向她怀抱的每一滴水。
E
我原来是在建筑工地干活,被打伤后,阿香不让我去干重活,劝我另找工作,所以我才干上了速递。
象往常一样,当我站在世贸商城那间办公室时,那位先生又给了我一大束玫瑰花,恐怕要超过100朵。我来不及数花,只想快点送到五角场那位老太手中。今天的活特别多,而且路程都不近,我担心那辆助动车又会罢工。
中午,在铜川路一家工地旁,有一个买盒饭的摊头,不少工地上的兄弟都在吃饭,他们和我一样,花五块钱要一大块皮厚肉肥的红烧肉,加一些蔬菜蹲在地上狼吞虎咽。他们舔尽最后一滴汤水,将最后一粒饭放进嘴里仔细的嚼着。然后心满意足的站起来,将空饭盒扔在路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纸烟,从烟盒里拿出几支,相熟的兄弟发一圈,然后用一只一次性塑料打火机客气的点上,美美的吸上一口,看着长长的烟雾从他们的鼻孔和嘴角呼出来,才觉得生活是多么的香甜。
我发现自己竟然还是那样喜欢建筑工地,喜欢这群搬砖头、和水泥,拿瓦刀的兄弟,喜欢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看着一片片荒芜的土地被我们唤醒,然后矗立起一座座高楼大厦。“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曾无比自豪的戴着安全帽,拿着扳手把脚手架越搭越高。
但我又为他们伤心。那次,我们建筑工地开进梅龙一片别墅区的外面,随着房子越造越高,那片别墅已完全暴露在我们的视线之中,特别是围墙边的那幢两层哥特式的小洋楼,我们几乎可以看见主人卧室的家具,更要命的是卫生间离脚手架更近。
那天中午,我见脚手架上还有两个人没下来,我就在下面大喊“下来吃饭,快。”他们俩急得直挥手,示意我别叫,但四只眼睛却一直盯着那间别墅不放。我觉得奇怪,爬上去一看,原来隔着窗纱有一对男女正在浴缸里干那事。“下去,有什么好看的。”但他们依然看得津津有味。
第二天中午,两人还象昨天一样蹲在脚手架上守株待兔,想再看一遍真人秀的三级片。没想到,有人埋伏在对面的阳台上,用汽枪向他们射击。两人中弹后,被急送医院,好在只伤在大腿和小腹,但泥瓦工是不能干了。
我去报了案,但直到大楼盖好,也没抓到凶手。
F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小心的拆开那只牛皮信封,里面有两本还飘着油墨香的《上海文学》,在第54页“海上诗坛”上竟然发表了我的组诗。在吴先生的点评中,特别提到了这首“谁收藏了冬天的羽毛”————
是谁收藏了冬天的羽毛
这座城市还能渴望的最后一点浪漫
都因为一场雪
一场没有准时赴约的雪
放弃,一张与美好有关的合同
一个诗人的仰视
让许多人抬起了头
但究竟寻找什么
只有天知道,十字路口
红绿灯对小汽车抛着媚眼
大酒店门前的服务**
和街旁的树一样,穿得特别的少
我们渴望一场雪
渴望一场超越对妻子想象的温柔
钢筋水泥武装到牙齿的城市
和金币才能碰出回响的心灵
正把摩天大楼上的广告女郎
称做亲爱的生活
纯洁,逐渐变成对雪的怀想
显得遥不可及
或者是枕边不知什么时候
怅然滑落的一滴泪
已经结冰
今年冬天不下雪
就是在一夜之间对世界的改变
缺少了一种可能
由于吴先生的推荐,我的一些诗和散文又陆续在《萌芽》《文学报》上发表了。我似乎成了上海打工文学者的代表,我忙着开会,写心得体会文章。我知道这不是吴先生的本意,但生活就是这样,总要从人生的舞台上不断选中一些幸运儿,把他们塑造成主要演员或者偶像,去让人崇拜。因为有人崇拜,要比没有人崇拜,让这个社会更安定团结。
G
直到我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二十五年,我才明白,生活在给你糖吃的时候,是为了灌你一碗更苦的药。
阿香在离开我一个月后,突然回到了我的身边。
“我真的要走了,再也不回来了。”
“为什么,我对你不好?”
“不”
我知道阿香会说不。是我带她出来打工,是我照顾她的生活,是我在她背叛我又被别人抛弃时去为她报仇,是我为了不触动她的伤口而更细心的呵护她。。。。。。
“我害怕和你在一起。”
“害怕和我在一起。我现在创作上刚有气色,再努力一把会成功的。”
“不,这和你的成功与否无关。我无法象当初一样爱你。”
“为什么,我不明白?”
“我怕你对我好,我的报答只是错上加错。”
“什么意思?”
“你以为温州老板会放了你?是我答应陪他朋友一个星期,此事才算一笔购销了。”
“啊!”我想,我当时也许只有一张呆若木鸡的脸,而根本发不出声音。
“我们不可能在一起,因为爱是平等的,爱是干净的。”
我无话可说。
阿香的背影依然美丽,但从今晚开始她将融入茫茫人海,我们也许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
那天,我在日记里写道:一个没有钱的男人,根本不配去爱,因为他根本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的爱情。
H
天工广告公司录取了我,因为我的创作成绩,但必须从广告业务员做起。
于是,我去了。
I
阿香走了,我每晚写作直到深夜。只有那些文字能够重温我的爱情,只有记忆里的花样年华才永远不会褪色。
阿香,你听见了吗
有一朵玫瑰在敲门
它唱着:爱情、爱情,我的季节
这是我精心抚育过的一缕花香
只为我们歌唱
阿香,这就是幸福啊
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吗
但我们要收藏的不是它的歌声
而是玫瑰内心无边的晴朗
阿香啊,在风中坚持是值得的
无论黑暗有多深有多疼
你、我、玫瑰都将互相照亮
我不知道发表在《新民晚报》上的诗,阿香是否看见。其实阿香看见了又能怎么样呢?
J
但诗还是给我带来了好运。李甜仪走进了我的生活。我们是在一次诗歌沙龙上认识的,我们一见倾心,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她怎么也没想到,那些优美轻盈的诗句竟然出自一个大老爷们之手,更巧的是甜仪也是天工广告公司的,而且是我的顶头上司,业务部经理。
“既然是我的部下,我怎么没见过你?”
“我刚进去,人事部还没让我去你那儿报到。”
“欢迎你,新同事。”她伸出手,我有些不好意思。刚刚人家还在我身边老师长老师短的叫个不停,没想到转眼间却变成了我的领导。唉,真是世事难料。
她的手握得很有力,有股男人的刚烈味。她非常漂亮,有着袅娜的身姿和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属于男人心里梦中情人的那种。
我喜欢和这样的女人打交道,我喜欢是因为喜欢她的漂亮;我害怕和这样的女人打交道,我害怕是因为害怕她的能干;漂亮和能干集于一身的女人,如不是魔鬼,就是天使,她可以把你的生活搞得一塌糊涂,也可以把你的生命弄得轰轰烈烈。经历过太多的失败,我已不再是一个多情的人,但我变得更敏感了。从她注视我的眼神中,我知道月老正悄悄的把一根红线扎在我们脚上。
那天,我拿着材料去业务部报到时,甜仪正在骂人,她骂人用普通话而且声音很响。
“你怎么这么容易上当?”
“我和他们签了协议。”
“屁的协议,这份协议根本没有约束作用。”
“这,对不起。”
“快滚,给我把人找来。”
我站在门外,进退两难。那位老兄低着头,从我身边溜了出去。甜仪看见了我,“进来。站在门外干什么?”
我心里想,我又没得罪你,于是我雄赳赳的走了进去。见我这模样,她到笑了,她一笑脸就象春天解冻的小河,笑意在她眼中荡漾开来,非常迷人。
“看什么,这里是办公室。”
我一下发觉了自己的失态,“今天先熟悉一下公司的情况,看看公司的资料,明天跟我去谈一个大客户,记着穿得精神一点。”
“好”我答到,我把属于我的那张办公桌上的灰尘擦干净,坐下来。
K
从那家跨国公司出来,我才知道甜仪是多么精明能干。只是我讨厌那个又矮又胖的杜边总经理,他和甜仪说话的时候,两只眼睛色迷迷的,如果不是隔着一张桌子,他肯定要爬到甜仪身上,我几乎看见他嘴角的馋水都滴下来了。
“这有什么,我见多了,糖衣炮弹打不倒我。对付这种人,就是把糖衣吃了,炮弹还给他,炸得他粉身碎骨。”坐在咖啡室里,甜仪显得很兴奋。如果象这样顺利,这份合同用不了多久就可以签下来了。我也很高兴,但心里总有点疙瘩。
“我不行,象这样的唇枪舌剑的谈判,我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
“也不是天生的,象写诗一样,用心就能很快进入角色。”
“诗和生活真的太远了,恐怕最无用的就是诗。”
“生活中当然不能没有诗,但诗却不是生活。走吧,我请你吃饭。”
“这”我还想客气一番,她一把从座位上拉起我,“走,有家水煮鱼很有特色。”
餐厅里人不多,也许这种南方菜在上海太平常,但对于我和甜仪这样的漂泊者来说却是很新鲜的。甜仪在大学是学广告的,毕业后到了天工广告公司。经过两年的奋斗,她成了这家大型广告公司的业务部经理。但从她对我的态度来看,她还是孤身一人。
她要了一瓶花雕,让**放几粒话梅和一些姜丝加热,酒入口温和绵长且有一股淡淡的香甜,象初恋的味道。但这酒有后劲,汤还没上来,她已是面若桃花,在朦胧的灯光下显得分外妖娆。
“别喝了,醉了我连你的家都找不到。”我按住她倒酒的手,眼里尽是爱怜。
“没事,应付那些客户,我喝过两瓶都没倒下。”她斟满酒,端起杯子“来,我们干一杯,为我们的相识。”
“干,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一定成相知。”我随口改了白居易的诗,一饮而尽。
“相识、相知、相亲、相爱,是不是男女经历了这四个阶段,就会携手走完一生?”她略有发红的眼睛盯着我。
“当然了,我的天使。”我把甜仪喊成了天使,她没有反对,我们只是长久的凝视着。
L
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头有些疼,大概是宿酒未醒,但我还是急忙赶到公司,我希望能够早一点见到我的甜仪,我的天使。
广告公司可真是一个出新闻的地方。公司负责一家著名运动鞋的宣传,电视、电台、报纸广告都做得非常成功,但这次他们要做出新意来,公司拿出的几个方案都被对方企划部经理枪毙了。于是,公司想到了发动群众,并打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标语,号召广告公司的所有员工都参与创意,拿出金点子有重奖。
我觉得机会来了,不是说机会总给那些有准备的头脑吗?其实我早准备好了,只是一直等待机会罢了。这年月,机会比才能重要100倍1000倍。如果拥有年轻还缺少什么的话,那就是机会、机会,还是机会。下午,我就拿着自己的创意,闯进了公司创意总监的办公室。
当你漫步在上海地铁,你会看到二十六张由世界飞人杰克蠢奔跑雄姿组成的巨幅,你站在外面看到的是静止的画面,但当你坐进地铁车厢,列车缓缓起步和靠站时,你将看到的是杰克蠢飞奔的连贯动作,象体育比赛中精彩镜头慢放一样。把运动明星的奔跑动作做成动画,再利用地铁列车的速度,将之组成一幅如同**一样活动的广告,这开创了沪上户外广告的先河,全国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广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当然,你看到的就是我的创意。
为了庆祝,我约天使去吃饭。她提出要去“水煮鱼”,但我坚持要去公司对面的“合和酒家”。虽然这酒家的名字特土,但很对我的心情。
其实,我害怕“水煮鱼”餐厅。说不上迷信,但我总在想,鱼离不开水,一辈子都生活在水中,没想到却也被煮死在水里。如果我和天使是两条共沐爱河的鱼,那么会不会也。。。。。。我隐约有种不祥的感觉。也许是我越爱她越害怕失去她吧,我自我安慰的想。
那顿饭吃完,我们真的象一对恋人了。我们手牵手走在外滩情人墙边,她告诉了我她家的地址和电话。
M
我和天使上班几乎见不到,因为我被调到创意部担任创意副总监。虽然在一家公司上班,但我们约会还是要用电话联系。
听天使讲,三季度刚过,业务部已经完成了一年的计划,而且那项300多万的合同这几天也要签下来了,我很为天使高兴。
N
阳光猝然出击
对黑夜是致命的,但我们
已经倒在岁月的伤口里
胸膛爬满追随春天的野草
谁都企图证明什么
通过我们悲哀的手,一切全变了
只有冰坚守最后一点精神
并且开始融化
那晚,和天使讨论完这首新作后,我已经有两天没有见到天使。起初,我没放在心上,因为天使是搞业务的,外面应酬多。
当我又熬完一个通宵,做好一个化妆品创意,阳光正洒满这座城市,我突然无比思念起天使来,我需要她来和我分享成功的喜悦。我拨通了她家的电话,但没有人接。我又拨通了她的手机,里面传来“机主已关机”冰冷的声音。等到9点钟,上班的时间早过了,但还是没见到天使。我再也坐不住了,跑出公司,扬手叫了一辆出租车。
我敲敲门,里面没有声音。我又用力敲敲门,里面还是没有声音。一种可怕的念头闪过我的心头,我一边使劲的捶门一边放声大喊“天使,开门。开门,天使。”我声嘶力竭的叫声,引来了房东。房东拿来钥匙,门开了——————
天使躺在床上,穿着那件雪白的毛绒绒的羊毛衫,淡红的唇,细眉轻描,她安详得象睡着了一样,但她失血过多的脸庞象她垂在床侧的左手一样苍白如纸,地上有一滩暗红的血,象一只被折断的蝴蝶的翅膀,不,不,那是一只被折断的天使的翅膀。
在写字台上,留着一封给我的短信“我走了,我被别人骗去了,不,我是被别人抢去了生命中最值得珍贵的东西。爱是干净的,所以我走了。不用伤心,天使是应该回到天堂去的!原谅我的不辞而别。你的天使。”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是怎样离开天使的。
我离开了天工广告公司,因为那里有太多回忆。
O
那天,我又去了五角场那幢房子,我呆了一会儿,我不敢去敲门,因为我已没有任何理由,我已不再是那个送玫瑰花的速递员了。我不知道那位年轻的先生是否还在给那个风韵犹存的老太送花,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否算爱情,如果是爱情,那爱情也太奇怪了。反正,我应该将这个谜珍藏在心底。
我在这座城市一边流浪,一边歌唱:
会飞的一切
都走了
包括时光
留下没有翅膀的我们
和一条路
程林,70年代出生,上海作协会员。著有诗集《想象的果实》,并有随笔、小说十余万字散见于全国各大报刊。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品搜搜测评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