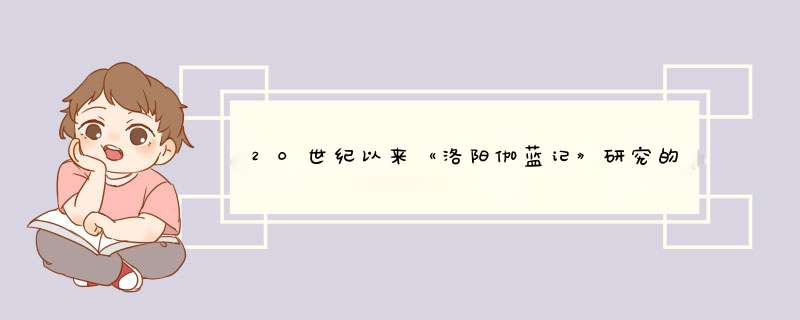
20世纪以来的《洛阳伽蓝记》研究,在其作者身世、文本笺注、文体特征、史学价值、人文地理及文学成就等方面均获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与南北朝的其他专书研究相比,其研究状况相对滞后,它在北朝史学、中古佛学、中古文学、语言学、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宗教建筑等课题上的研究价值和研究空间仍需大力开拓和进一步深化。[关键词]20世纪;《洛阳伽蓝记》研究;回顾;展望《洛阳伽蓝记》是我国历史上一部以记载佛寺为纲、具有文化与文学价值的历史地理名著,是与《水经注》、《颜氏家训》相齐名的北朝三部杰作之一,一直为世人所瞩目。它既有优美之文笔,更有丰富的内涵、珍稀的史料,在历史、文学、地理、佛教、交通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价值,是北朝文献中极其珍贵的精品。本文试图对20世纪以来《洛阳伽蓝记》(以下简称《伽蓝记》)研究作一回顾,并展望《伽蓝记》的研究前景。一、《伽蓝记》研究综述近百年的《伽蓝记》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以前的近50年为第一阶段,此阶段的研究重在校勘、注释与考证,为后来的研究积累了一定基础;第二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此时期出现了几个重要的《伽蓝记》整理和校注的本子,但国内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伽蓝记》研究显得沉寂、低迷,一些观点也较为偏颇;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由于学术思想得到解放,研究成果不断增多,研究视野和思路不断拓宽,取得的成绩较为显著。自《伽蓝记》问世流传1000余年来,在学术史上一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偶有涉猎者,只是著录、序跋、题识,略记其概,缺乏一个整理的善本。直至近代,《伽蓝记》方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因此《伽蓝记》研究第一阶段的近50年,学者多在校勘版本、训解文字、考案史实和注释笺疏等方面用力,这些对《伽蓝记》的研究可谓具有筚路蓝缕之功。20世纪上半叶,较早对《伽蓝记》进行校勘和整理的,是1915年唐晏所撰的《洛阳伽蓝记钩沉》。1930年张宗祥综合诸家版本,作《洛阳伽蓝记合校》。1937年,周延年撰《洛阳伽蓝记注》,这是对《伽蓝记》全面加以诠解的第一个注释本。其后屠敬山撰写《伽蓝记》注及校勘记各五卷,惜稿本于赴蒙古途中被盗贼劫去。由于受到西方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撰写有系统的《伽蓝记》专题论文。如1939年陈寅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2分册发表的《读<洛阳伽蓝记>书后》,1943年孙次舟在《金陵女大集刊》第一辑发表的《洛阳伽蓝记子注释例》,1944年郑骞为纪念周作人60岁诞辰撰写的《洛阳伽蓝记丛考》等。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伽蓝记》在整理和校注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科学出版社,1958)和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是两种已有广泛影响的《伽蓝记》校注本。在研究论文方面,黄公渚在《文史哲》1956年11期刊出了《<洛阳伽蓝记>的现实意义》,该文分七个部分论述了《洛阳伽蓝记》及其作者的思想,是一篇较有深度而又全面的论文。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序》用了20 000多字,从五个方面介绍和评论杨街之及其所著《洛阳伽蓝记》,是继黄公渚之后《伽蓝记》研究的一部力作。1960年1月31日,罗根泽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洛阳伽蓝记)试论》,论述了北魏建佛寺的意义以及杨街之写作《洛阳伽蓝记》的目的。由于受左倾思想的限制,此时期对《伽蓝记》的评价不高,如社科院编文学史认为“书中也常常表现出杨街之的一些落后思想”,“写佛像流泪等迷信故事也很多”。“新时期”以来的20多年里,《伽蓝记》研究逐渐得到人们的关注,各种专题论文纷纷涌现,研究视角呈现出多样化,研究内容也逐渐丰富起来。在这些论文中,对以下几个问题的探讨尤为引人注目:(1)《伽蓝记》的作者姓氏、籍贯和生平问题;(2)杨街之的思想与《伽蓝记》的创作主旨;(3)《伽蓝记》版本、笺注及文体问题;(4)《伽蓝记》的史学和文化史价值;(5)《伽蓝记》的建筑和园林艺术研究;(6)《伽蓝记》的文学成就;(7)《伽蓝记》的中古语言学价值。在这些众多的论文中,罗晃潮《<洛阳伽蓝记>版本考述》(《文献》1986年第1辑)对《伽蓝记》流传的不同版本系统作了清晰的梳理;李晓明《(洛阳伽蓝记>的特点》(《史学史研究》1994年3期),从史学的角度探讨了《伽蓝记》的特点和价值;曹虹《<洛阳伽蓝记>新探》(《文学遗产》1995年4期),从新的视角作了探索,指出:“作者面对的这一片佛教建筑,既是一种宗教景观;又是一种更为广泛的人文景观。”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北方论丛》1996年5期)对《伽蓝记》文体的形成及文化渊源进行了深入研究;曹道衡《关于杨街之和<洛阳伽蓝记>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2001年3期)对《伽蓝记》及其作者生平思想等六个问题作了精审考证和论述;等等。这些论文均能自出机杼,别立新意,把《伽蓝记》研究引向深入。台港地区及国外日本、欧美等国家的《伽蓝记》研究也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绩。在港台地区,有几种《伽蓝记》整理版本很值得注意,如徐高阮精校的《重刊洛阳伽蓝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二,1960),田素兰的《洛阳伽蓝记校注》(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1972),香港中文大学杨勇的《洛阳伽蓝记校笺》(台北:正文书局,1982)。此外,徐高阮的《<洛阳伽蓝记>补注体例辨》(史语所集刊22本,1950)、王伊同的《诠释(洛阳伽蓝记)志余》(《清华学报》1983年12月第15卷)、詹秀惠的《<洛阳伽蓝记>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院刊》第1期,1983年6月)、林文月的《(洛阳伽蓝记)的冷笔与热笔》(《台大中文学报》第l期,1985年11月)等论文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与祖国大陆的成果相映成辉,构成20世纪《伽蓝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伽蓝记》至少有三种版本:日本学者入矢义高译注的《洛阳伽蓝记》(平凡社,1974),英国W。J。F。Jenner译注的Memories 0f Loyang:Yang Hsiian——chih and the Lost Capital(493—534)(Oxford:ClarendonPress,1981)、美国华裔学者王伊同的译本A Record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Lo——yang(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84),显示出国际汉学界对此书亦颇为重视。二、《伽蓝记》研究的热点问题(一)《伽蓝记》作者姓氏、籍贯和生平的研究杨街之虽因著《伽蓝记》而名传后世,但正史中无传,人们只能靠历代书目著录和《广弘明集》中极简略的小传等零散的记载来研究其姓氏、籍贯和生平等问题。从隋唐以来的各种著作所记看,街之的姓有“杨”、“阳”、“羊”三种写法。究竟衙之为何姓?历来就有争论。但争论者一般弃置“羊”姓不论,多主“杨”姓或“阳”姓。主“杨”姓一派者自《四库提要》始,认为:“刘知几《史通》作羊街之,晁公武《读书志》亦同,然《隋志》亦作杨,与今本合,疑《史通》误也。”其后清人李文田、今人余嘉锡、范祥雍、刘跃进、詹秀惠等倾向“杨”姓说。主“阳”姓一派者最早出自周延年《杨街之事实考》:“详考《北史》及《魏书》杨氏达者无北平籍,……则北平之阳氏以文章传家,已可概见。街之若果为阳姓,其为休之之弟及族昆弟,必无疑矣。”郑骞、黄公渚、周祖谟、王仲辇、范子烨等力主“阳”姓。街之的籍贯,据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六《辨惑篇》说是“北平人”。但《魏书·地形志》载,北魏时有两个“北平郡”:一属平州,一属定州。主“杨”姓说者,大多认为街之属定州之北平;主“阳”姓说者,则多认为应属于平州之北平。街之的生平,周祖谟《杨衙之事实考》和范祥雍《杨街之传略》记述最为翔实,一般认为,衙之曾任过奉朝请、期城太守、抚军府司马和秘书监四个官职。而曹道衡据北魏史实考证,街之任秘书监一职很不可信。(二)《伽蓝记》创作主旨与文体的讨论《伽蓝记》的创作主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寄托怀念故国的情思,二是街之对待佛教的态度。第一个主旨从《伽蓝记》序中可以明显看出,毫无疑义。而人们对《伽蓝记》的佛教态度,则争议颇大。一种意见认为街之著《伽蓝记》的宗旨是为了排佛。如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认为:“杨街之的《洛阳伽蓝记》,为公认的反佛的激烈文献。”黄公渚《(洛阳伽蓝记)的现实意义》、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序》均赞同侯说。当代学者范子烨则提出街之当为天师教道徒,他撰写《伽蓝记》“同时为了给自己尊奉的道教鸣不平”。另一种意见认为《伽蓝记》并没有反佛的宗旨。如罗根泽《<洛阳伽蓝记>试论》认为“忠于拓拔王朝和对佛教的尊信”是《伽蓝记》的一个重要内容。曹道衡《关于杨街之和(洛阳伽蓝记)的几个问题》持相似观点,认为《伽蓝记》“并不反佛,而是反对王公贵族的奢靡”。《伽蓝记》的文体是20世纪以来《伽蓝记》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唐代刘知几《史通·补注篇》称此书的文体是“定彼榛梏,列为子注”,即杨街之著书时曾自为子注。大概到了宋朝,正文与子注混在一起,不复分别。四库馆臣不察,竞称“不知何时佚脱”。清代校勘学家顾广圻《洛阳伽蓝记跋》指出:“此书原用大小字分别书之。今一概连写,是混注入正文也。”此后许多学者致力于恢复《伽蓝记》原貌的工作。如吴若准《集证》,划分段落,区分正文与子注。然所定正文太简,注文过繁,恐距杨书原貌甚远。后唐晏作《钩沉》,在吴氏的基础上重新把正文与子注作了划分。吴氏《集证》本、唐晏《钩沉》本之后,周祖谟《校释》本、徐高阮《重刊》本,均致力于阐明杨书体例,再次详分子注,以期能尽量再现原书面目。(历史论文 )杨勇《校笺》本综括前贤,后出转精,确定六条划分原则,正文子注区分更加科学合理。但也有学者主张在未找到更古的《伽蓝记》本子时不宜强行分别,如张宗祥《合校》书后跋纵论《伽蓝记》正文与子注不易区分的理由,其说颇允。范祥雍《校注》信从张说,不作正文子注的区分。关于《伽蓝记》文体的渊源,陈寅恪先生在《支愍度学说考》和《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二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发覆,认为此种新文体源于六朝时期的“合本子注”体佛学著作;同时,它也是当时学林流行的“合本子注”体著作的具体表现。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北方论丛))1996年5期)和《(洛阳伽蓝记>的文体特征与中古佛学》(《文学遗产》1998年6期),在陈寅恪研究的基础上对《伽蓝记》文体的形成及其文化渊源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三)《伽蓝记》史学价值的探讨20世纪以来史学界对《伽蓝记》的史学价值作了较多的讨论。首先,在史学理论方面,台湾学者何寄澎《试论杨街之的历史精神》(《思与言》,1983年3月第20卷第6期)提出杨氏是在一份浓厚历史感的驱策下创作《伽蓝记》的,其撰作的真正目的乃是要传述一段“信史”。李晓明《(洛阳伽蓝记>的特点》(《史学史研究》1994年3期),认为《伽蓝记》有以下几方面的史学特点和价值:(1)因地叙事,以地系史;(2)采取多样形式,寓褒贬于叙事之中;(3)广泛的史料来源和多方参证、勇于存疑的治史态度相结合;(4)丰硕的历史文学成就。王美秀《从质疑历史到争夺诠释权——以(洛阳伽蓝记)的历史论述为例》(《台大中文学报》,2002年11月第18期),指出杨街之身处中国民族激烈冲突的时代,在北魏长期汉化之后又遭遇所谓鲜卑化的文化逆流,其牵动的文化认同问题势难规避,此书显露的历史特质与此深有渊源。其次,《伽蓝记》在佛教史研究领域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如潘桂明《<洛阳伽蓝记>与北朝佛教》(《魏晋南北朝佛教史论文选集》,《中原文物》特刊,1985年)根据《伽蓝记》记载的有关佛教事迹,为我们勾画了佛教在北魏洛阳繁盛的图景。卢宁《由(洛阳伽蓝记>看北魏的中原法化》(《法音》1998年12期)从《伽蓝记》保存的有关建筑园林、教法流播、民俗风情等大量宝贵资料分析,认为北魏统治者推行的汉化与佛教法化对中原地区产生过巨大影响。再次,人们对《伽蓝记》所反映的北魏社会经济、风俗民情、音乐艺术、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也多有探究。如黄公渚《(洛阳伽蓝记>的现实意义》,从揭露统治者的丑恶、反映都市经济面貌、记录各阶层的动态和社会风尚等方面探讨了《伽蓝记》的社会现实意义。常新《<洛阳伽蓝记)的社会文化史意义》(《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8期)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角度,认为《伽蓝记》记述的北魏定都洛阳期间的政治、人物、风俗、掌故传闻及北魏和西域文化交流等,可以说是一部反映该时期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伽蓝记》卷五作为南北朝时期中外交通与文化交流的珍贵文献,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和重视,如丁谦《宋云求经记地理考证》(载《浙江图书馆地学丛书》第二集,1915年)、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六册《宋云、惠生》(中华书局,1979)、法国沙畹(E。Chvannes)《宋云行纪笺注》(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六编》,中华书局,1956)等均是这方面的突出成果。(四)《伽蓝记》的城建规划、建筑和园林艺术价值研究《伽蓝记》以佛寺为中心,记述北魏京城的建筑,次序整然,体例明晰,是研究北魏洛阳城市规划、建筑和园林艺术的重要资料。劳干《北魏洛阳城图的复原》《史语所集刊》20本上册,1948)以怀履光的测量图为前提,利用《伽蓝记》和《帝王世纪》、《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晋元康地道记》等资料绘出了北魏洛阳城复原图。何炳棣《北魏洛阳城郭规划》(《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台北:清华学报社,1965年)根据《伽蓝记》的记载,确定了洛阳的规模和建置,提出北魏洛阳的坊里制不只是土地利用制度,而是根据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不同社会经济性能的全盘都市设计。孟凡人《北魏洛阳外郭城形制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2年4期)参照《伽蓝记》记载,结合墓志以及部分地区的实地考察,对洛阳外郭的形状、郭门、城墙和主要建筑布局等进行了探究。张金龙《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探微》(《历史研究》1999年6期)结合《魏书》和《伽蓝记》记载,对学术界研究歧见较大、或未曾注意又关涉洛阳里坊制度认识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探索。薛瑞泽《读<洛阳伽蓝记>论北魏洛阳的寺院园林》(《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2辑)认为北魏洛阳寺院园林的构成有两种形式,此时的寺院园林具有达官贵人园林的特色。此方面,日本学者亦用力颇多,如水野清一《洛都永宁寺解》(1939年初次发表,《中国的佛教美术》,1968)、森鹿三《关于北魏洛阳城的规模》(1952年初次发表,收入《东洋学研究》历史地理篇,1970)、服部克彦《北魏洛阳的社会与文化》(1965)和《续北魏洛阳的社会与文化》(1968)等均是以《伽蓝记》为主要史料的翘楚之作。(五)《伽蓝记》的文学成就研究《伽蓝记》在文学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四库馆臣评“其文裱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但由于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多重南朝而轻北朝,《伽蓝记》亦因此沦为遗珠。直至20世纪80年代,《伽蓝记》的文学价值才逐渐得到学界较多关注。林文月《<洛阳伽蓝记>的冷笔与热笔》认为,杨街之以冷笔写空间,故条理井然,是《伽蓝记》极具研究价值处;以热笔写时间,故好恶分明,是杨街之有别于后世修史之枯淡处,冷热交织,遂令这部稀世珍贵的奇书呈现特殊面貌而永垂不朽。曹虹的《(洛阳伽蓝记>新探》则认为,整体组织上的善于经纬,融史笔与文采于一炉的局部描述,是《伽蓝记》一书的不可多得之处。韩国学者成润淑《<洛阳伽蓝记)的小说艺术研究》(《文史哲》1999年4期)在范祥雍研究的基础上对《伽蓝记》的小说史价值作了专题研究,认为《伽蓝记》已符合小说演进中的各种特质,不论从题材上还是从艺术手法,都已成为介乎六朝残丛小语与唐传奇之间的过渡形态。林晋士《(洛阳伽蓝记>在文学史上之价值》(《屏东教育大学学报》2006年9月第25期)对《伽蓝记》文学史价值进行了全面研究,指出,《伽蓝记》不但在散文史和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即从文学史料的角度而言,《伽蓝记》记载的古籍逸文与俗谚歌谣,也为后世的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资料。20世纪以来,经过许多学者的艰苦工作,《伽蓝记》研究成果不断增多,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领域不断开阔,研究视野和思路不断拓宽。但是,还存在诸多问题,目前的《伽蓝记》研究只有零散的单篇论文出现在学术期刊上,有些论文还停留在概述和知识性介绍的水平,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传世名著,《伽蓝记》的研究状况与其本身的文学地位也是不相称的。它的研究程度远不能与南北朝时期《文心雕龙》、《诗品》、《世说新语》等专书研究相比,甚至与《水经注》相比,它的研究也显得冷落得多。展望21世纪的《伽蓝记》研究,它在北朝史学、中古佛学、中古文学、语言学、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宗教建筑等课题上的研究价值和研究空间仍需大力开拓和进一步深化。随着人们对《伽蓝记》的深入认识,21世纪的《伽蓝记》研究定会大放异彩,向世人展现其应有的魅力。
伽蓝的解释
[梵samghrma]
梵语僧加蓝摩的略称,意译众园或僧院。佛教寺院的通称 我不如走到伽蓝殿中,问个终生的吉凶。——《英烈传》 详细解释 (1)梵语僧伽蓝摩译音的略称。意为众园或僧院,即僧众居住的庭园。后因称佛寺为伽蓝。 北魏 杨炫之 《洛阳伽蓝记·法云寺》 :“伽蓝之内,花果蔚茂, 芳草 蔓合, 嘉木 被庭。” 唐 玄奘 《大唐西域记·阿耆尼国》 :“伽蓝十馀所,僧众二千馀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翻译名义集·寺塔坛幢》 :“僧伽蓝译为众园。 《僧史略》 云:‘为众人园圃。园圃,生植之所;佛弟子则生殖道芽圣果也。’” 元 王实甫 《西厢记》 第二本第一折:“三日之后不送出,伽蓝尽皆焚烧。” 鲁迅 《集外集 拾遗 补编·儗播布美术意见书》 四:“伽蓝宫殿,古者多以宗教或帝王之威力,令国人成之;故时世既迁,不能更见,所当保存,无令毁坏。” (2)伽蓝神的省称。 《西游记》 第九八回:“ 佛爷 爷大喜,即召八 菩萨 、四金刚……十八伽蓝,两行排列,却传金旨,召 唐僧 进。” 《敕修百丈清规》 卷二:“伽蓝土地,护法护人。” 明 无名氏 《精忠记·说偈》 :“夜来伽蓝托梦, 故人 岳 鹏举 来此径过,须当迎接。” 清 侯方域 《重修白云寺碑记》 :“三年乃创大殿,建立三佛像,与夫金刚、 罗汉 、韦驮、伽蓝之属。”
词语分解
伽的解释 伽 é 〔伽南香〕沉香。 〔伽蓝〕梵语“僧伽蓝摩”的简称,指僧众所住的园林,后指佛寺。 伽 ā 〔伽倻〕 朝鲜 乐器名,有些像 中国 的筝。 伽 ā 〔伽马射线〕即“丙种射线”,镭和其他一些放射性元素的原 蓝的解释 蓝 (蓝) á 用靛青染成的 颜色 , 晴天 天空 的颜色:蓝 盈盈 。 蔚蓝 。蓝本。蓝图。 植物名,品种很多,如“蓼蓝”、“菘蓝”、“木蓝”、“马蓝”等。 古同“褴”,褴褛。 姓。 笔画数:; 部首 :艹; 笔顺编
我来回答,一作者在洛阳伽蓝记中描述了北魏几个王侯的奢侈生活 腐朽思想和贪婪的性格,这样写的作用是什么?
作者通过了剖析王候们奢侈的生活和腐朽思想及贪婪性格,来警示贪官们,人间正道是沧桑,凡违背人民的意愿的跳梁小丑们都不会有好下场,终将被历史的车轮碾的粉身碎骨,遗臭万年!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品搜搜测评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