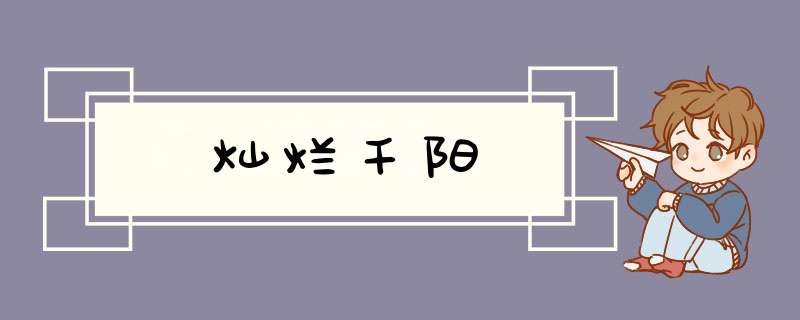
五岁那年,玛丽雅姆第一次听到“哈拉米”这个词。
那天是星期四。肯定是的,因为玛丽雅姆记得那天她坐立不安、心不在焉;她只有在星期四才会这样,星期四是扎里勒到泥屋来看望她的日子。等到终于见到扎里勒的时候,玛丽雅姆将会挥舞着手臂,跑过空地上那片齐膝高的杂草;而这一刻到来之前,为了消磨时间,她爬上一张椅子,搬下她母亲的中国茶具。玛丽雅姆的母亲叫娜娜,娜娜的母亲在她两岁的时候便去世了,只给她留下这么一套茶具。这套瓷器的颜色蓝白相间,每一件都让娜娜视若珍宝,她珍爱茶壶嘴美观的曲线,喜欢那手工绘制的云雀和菊花,还有糖碗上那条用来辟邪的神龙。
从玛丽雅姆手中掉落、在泥屋的木地板上摔得粉碎的,正是最后这件瓷器。
看到糖碗,娜娜满脸涨得通红,上唇不停地抖动,那双一只暗淡、一只明亮的眼睛死死地、眨也不眨地瞪着玛丽雅姆。娜娜看上去十分生气,玛丽雅姆害怕妖怪会再次进入她母亲的身体。但妖怪没有来,这次没有。娜娜抓住玛丽雅姆的手腕,咬牙切齿地说:“你这个笨手笨脚的小哈拉米。这就是我忍受了一切得到的回报。一个打碎传家宝的、笨手笨脚的小哈拉米!”
当时玛丽雅姆没有听懂。她不知道“哈拉米”——私生子——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她还小,不能理解它所包含的歧视,也并不明白可耻的是生下了哈拉米的那些人,而非哈拉米,他们惟一的罪行不过是诞生在这个人世。但由于娜娜说出这个词的口气,玛丽雅姆确实猜想到哈拉米是一种丑陋的、可恶的东西,就像虫子,就像娜娜总是咒骂着将它们扫出泥屋的、慌慌张张的蟑螂。
后来,玛丽雅姆长大了一些,总算明白了。娜娜说出这个词语的口气已经让玛丽雅姆觉得它特别伤人——更何况她还边说边吐口水。那时她才明白娜娜的意思;才懂得哈拉米是一种人们不想要的东西;才知道她,玛丽雅姆,是一个不被法律承认的人,永远不能合法地享受其他人所拥有的东西:诸如爱情、亲人、家庭、认可,等等。
扎里勒从来没这样叫过玛丽雅姆。扎里勒说她是他的蓓蕾。他喜欢她坐在他的膝盖上,喜欢讲故事给她听,喜欢告诉玛丽雅姆说赫拉特[1]Heart,阿富汗西部城市。[1],也就是玛丽雅姆1959年出生的那座城市,一度是波斯文化的摇篮,也曾经是众多作家、画家和苏非主义者的家园。
“你要伸出一条腿,准能踢到一个诗人的屁股。”他哈哈大笑说。
扎里勒跟她讲加瓦尔·沙德皇后[2]GauharShad(1378~1457),也作GawarShad或GoharShad,帖木儿汗国国王沙哈鲁之妻,兀鲁伯之母。[2]的故事,他说15世纪的时候,她建造了许多著名的尖塔,当做是献给赫拉特的颂诗。他向她描绘赫拉特绿油油的麦田和果园,还有那藤蔓上结满果实的葡萄,城里带圆形拱顶的拥挤市场。
“那儿有一棵开心果树,”有一天扎里勒说,“在树下面,亲爱的玛丽雅姆,埋着的不是别人,正是伟大的诗人雅米[1]LahmanJami(1414~1492),拉赫曼·雅米,波斯诗人。[1]。”他身体前倾,低声说:“雅米生活在五百年前。真的。我带你去过那儿,去那棵树。那时你还很小。你不记得了。”
这是真的。玛丽雅姆不记得了。虽然她在一个步行便可以到达赫拉特的地方度过了生命中的十五个年头,玛丽雅姆将不会见到故事中的这棵树。她将不会走近参观那些著名的尖塔;她也将不会在赫拉特的果园拾果子或者在它的麦田里散步。但每逢扎里勒说起这些,玛丽雅姆总是听得很入迷。她会羡慕扎里勒的见多识广。她会为有一个知道这些事情的父亲而骄傲得直颤抖。
“说得跟真的一样,”扎里勒走后,娜娜说,“有钱人总喜欢说谎。他从来没带你去过什么树下面。别中了他的。他背叛了我们,你深爱着的父亲。他把我们赶出家门。他把我们赶出他那座豪华的大房子,好像我们对他来说什么也不是。而且他这么做还很高兴呢。”
玛丽雅姆会毕恭毕敬地听着这些话。她从来不敢对娜娜说自己有多么厌恶她这样谈论扎里勒。实际上,在扎里勒身边,玛丽雅姆根本不觉得自己像个哈拉米。每个星期四总有那么一两个小时,当扎里勒带着微笑、礼物和亲昵来看望她的时候,玛丽雅姆会感到自己也能拥有生活所能给予的美好与慷慨。因为这个,玛丽雅姆爱扎里勒。即使她只能得到他的一部分。
扎里勒有三个妻子和九个子女,九个合法的子女,对玛丽雅姆来说,他们全都是陌生人。他是赫拉特屈指可数的富人。他拥有一家**院,玛丽雅姆从未见过,但在她的恳求下,扎里勒曾经向她描绘过它的形状,所以她知道**院的正面是蓝色和棕色相间的陶土砖,还知道它有一些包厢座位和格子状的天花板。推开两扇摇摇摆摆的门,里面是贴着地砖的大厅,大厅里面有些玻璃橱柜,展示着各种印度**的海报。有一天扎里勒说,每逢星期二,儿童观众可以在零食部得到免费的冰淇淋。
他说到这句话时,娜娜忍住笑容。等到他离开泥屋,她说:“陌生人的孩子得到了冰淇淋。你得到了什么呀,玛丽雅姆?你得到的是冰淇淋的故事。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品搜搜测评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