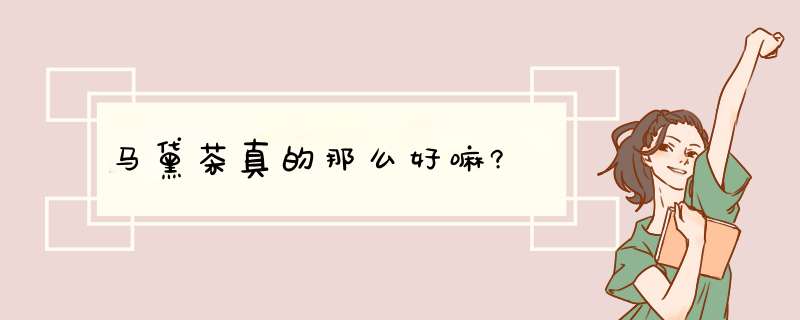
马黛茶富含维他命A, C, E, B1, B2, B3, B5,钙, 锰, 铁, 硒, 钾, 镁, 氟, 锌[1](根据马黛茶茶商,也有相当多的咖啡因,但是相比于喝咖啡,喝mate之后咖啡因不会有冲头感,而且咖啡因带来的清醒度,能维持更长的时间(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具体有多大的养生功能,有没有超越绿茶,各家有各家的说法,比如[1]就说比绿茶有营养,但是你懂的,有自吹自擂嫌疑。
南美人民是如此热爱马黛茶,好处肯定多多啦,至于和绿茶相比,哪一个更出色,这个没有进一步数据很难回答。
不过就个人来说,我喝马黛是因为马黛是很好的咖啡/红牛替代品,无热量,纯天然,口味也很不错,能让我长时间头脑清醒。
话说梅西,马斯切拉诺,内耳马和苏亚雷斯一干南美球星比赛之前都会一起分享一杯马黛,精气神就是足啊,你看这几个赛季巴萨的成绩,马黛茶也算是功不可没。
本文标签: 马黛茶 , 马黛茶的性质近日一些马黛茶友们向我们咨询,马黛茶到底是凉性的还是热性的呢?下面就这个问题给广大茶友一个解答。凉性、热性或者说寒性、热性这个都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讲的。而马黛茶是阿根廷南美的一种植物,阿根廷人不懂中医,自然无法解答。但是根据马黛茶阿根廷人的饮用习惯,可以管窥一二。如果说是属于凉性,那么阿根廷球员上场是肯定不能带着当饮料喝的,因为踢球要讲求力量,如果是凉性泻火的,没了火气,甚至还拉肚子,哪里会有球员敢喝呢?更不要说梅西、马拉多纳天天把马黛茶当宝贝捧着喝了,我想朋友们肯定没有见有球员上场带着冰镇王老吉吧?马黛茶是寒性的还是热性的?那么如此说,马黛茶就是属热性了?又非也。阿根廷这个民族的人们常年食用大量的肉食,大家都知道肉食生燥热的,如果我们吃一大堆肉,再喝一些热性的饮料,那岂不是火上浇油吗?我们一般很少是吃了羊肉火锅然后再来两斤荔枝龙眼加杯长白山参茶的吧?阿根廷人吃巨量的肉,而他们良好的血液品质又恰恰说明了,吃肉喝马黛茶没有火上浇油,反而让他们更加健康。所以,综上所述,既不是凉性,也不是热性。那是什么性质呢?中性。也就是说,你即使是凉性、寒性或者热性、抑郁体质,喝马黛茶并不能加强您的体质的这些方面,也不会从相反的方向给予弥补。那又有朋友问了,既然没有弥补,为什么我是寒性、热性、抑郁性的体质喝马黛茶又有健康的效果呢?很简单,因为马黛茶本身的营养物质能够平衡您身体不均衡的体质,只有平衡了您的体质,身体才会健康哦。详细可以了解一下马黛茶的健康效果医学报告,这个可是根据我们帕拉纳马黛茶调研得出来的,值得一看!
马黛茶和茶的共同点,阿根廷国宝“马黛茶”一进入中国便大受追捧,这使人十分诧异。中国本来就是茶之大国,从古至今,制茶技术都是一流的,为何南美的马黛茶才引进就能打开中国市场大受国人喜爱马黛茶与咖啡、茶(中国的红茶、绿茶等)并称为“世界三大茶”。大家都想知道如此受欢迎的马黛茶与我们熟悉的国产茶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1、从种类上
马黛茶不是茶,是一种植物,用南美洲热带雨林气候中独有的马黛树的叶子精制而成,只是因为饮用方式与茶相同故称“马黛茶”。
2、从功能上
“马黛茶”是纯植物健康饮品,含有196种活性物质,可以补充精力、提神助眠、消食解腻、轻体养颜、净化血液、提高免疫。而普通的茶叶主要作用是解渴休闲
“我又把插在马甲左腋窝下的那把锋利的短刀抽出来,端详了一番,那把刀跟新的一样,精光锃亮,清清白白,一丝血迹都没有留下。”
博尔赫斯,一个站在过去却能看见未来的人。他被称为“作家们的作家”,有着极大的创造力和颠覆性,这个靠着大量阅读来获取知识,独身多年,晚年失明却依然成果不断的先锋派作家,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登陆中国,十几年间便名声大噪,生根开花。
30多岁的博尔赫斯,为了再现半个世纪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而写下《玫瑰色街角的汉子》,这个充满浪漫气息的名字背后讲述的却是一个扣人心弦,情节诡异又十分烧脑的故事。在西班牙语中“玫瑰色街角”指的是位于街角的百货店墙壁,多年前,这里既是商店又是酒馆。当胡丽娅舞厅外的红灯再次亮起,音乐声混杂着酒精在空气中弥漫,夜幕遮挡下,舞厅常驻客们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文章开头,赫赫有名的牲口贩子雷亚尔前来舞厅寻找好汉罗森,并当面向其立下战书。众人盼着罗森多动手之时,他却像懦夫一样拒绝了挑战,这一行为惹怒了其女友卢汉纳拉,她将刀子递给罗森多激励其应战,而罗森多依然拒绝,并将刀子从窗口扔出,掉入河内。卢汉纳拉愤怒了,她投入了雷亚尔的怀抱,两人“脸贴着脸”出去了。“我”因为心目中的偶像“罗森多”轰然崩塌而郁闷无比,走出舞厅透气,当“我”再次返回时,却“发现”雷亚尔中刀身亡,警察赶来,卢汉纳拉乘乱溜走,“我”悠闲的溜达回家,发现窗口亮着灯光便立刻加快了脚步。
太多的故事发生在文字之外
从雷亚尔来到舞厅,到被杀身亡警察赶来,博尔赫斯用了不到5000字便把故事讲完了。大量的细节被隐去,故事变得破碎而跳脱,只留下最根本的框架和指引你走出迷宫的线索。卢汉纳拉和雷亚尔离开后,“我”走出舞厅遇到了罗森多,他在我身边嘀咕:“你这个混小子老是碍事。”而之后呢?罗森多看到雷亚尔被刺了吗?他是否去找了卢汉纳拉?他最后去了哪?博尔赫斯什么也没说,他只告诉我们“他(罗森)顺着比较幽暗的马尔多纳多河一边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在舞厅之外,故事依然在继续,凶手是怎样杀害雷亚尔的?卢汉纳拉都看到了什么?而“我”又去了哪里?这些关乎故事完整性的重要信息统统被隐匿了,甚至连简单的一句概括也没有。故事立马跳转回舞厅之内,将死的雷亚尔,哭着进门的卢汉纳拉和装作没事的“我”。一整段完整的情节被跳过了,就像王家卫的**一般,女主角的脚步临近房间,下一个镜头她便出来,留你在屏幕前猜测房间内发生的故事。
为什么要把这些重要的情节统统省略?博尔赫斯大概是在引导你去猜,引导你在一遍一遍的反复阅读中拨开迷雾,就像是出了一道填空题,填对了,便会豁然开朗。而最重要的正是这豁然开朗的瞬间,若是把空缺的部分全都补上,凶手是谁自然一目了然,但没有了反复的推敲猜测,故事也就变得平平无奇了。
找到线索,是走出迷宫的唯一方式
作为一篇推理小说,《玫瑰色街角的汉子》让反复琢磨,猜测的读者最终恍然大悟,这无疑是其成功之处,大量的叙事空缺增加了故事的理解难度,为了让读者走出迷宫,博尔赫斯别有用心的在文中提供了线索和暗示,指引你找到最终的凶手。
雷亚尔死了,卢汉纳拉目睹了一切,文中写道“她发誓说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反正不是罗森多。可谁会信她的话?”凶手似乎指向了罗森多,但卢汉纳拉本就是因为男友的怯懦而投入雷亚尔的怀抱,若是罗森多杀死了雷亚尔,卢汉纳拉又怎会失魂落魄。那卢汉纳拉自己呢?当她被怀疑时,文中的“我”挺身而出为其辩解“我带着讥刺的口气说:“你们大伙看看这个女人的手,难道她有这份气力和狠心捅刀子吗?””确实,雷亚尔高大壮实,满面愠色怎会死在一个女人手下。最终,凶手指向了这个从头到尾不露半点声色的无名小卒——文中的“我”。
这令人惊愕的猜测在仔细的推敲和揣摩中竟一步步验证。故事的开头,作者便埋下伏笔“我只跟他(雷亚尔)打过三次交道,三次都在同一个晚上,”除去雷亚尔初次进入舞厅以及最终死在舞厅之外,另一次交道便只能是舞厅之外的刺杀。而在故事的结尾提到:“窗口有一盏灯光,我刚走近就熄灭了。我明白过来之后,立刻加紧了脚步。”这人是谁?再次回看开头,不禁恍然大悟“那晚的事我怎么都不会忘记,因为卢汉纳拉在我家过夜”那人竟是卢汉纳拉,她目睹了一切,从舞厅溜出后便来到了“我”家。
在得知结果后回看全文,不禁感叹作者缜密的逻辑和无处不在的暗示。“我想自己无非是长在河岸边的蛤蟆花和骷髅草中间的又一株野草罢了。”“我”的偶像——这个男人和狗都尊敬的人,一夜之间便崩塌了。这让“我”失去了精神支柱的同时又感到恼羞成怒。杀死雷亚尔,像是一种对自己英勇血性的最好证明。
除此之外,故事中很多细节都在暗示着凶手的身份“我装着没事的样子混进人群”,“我在期待,但不是期待后来出的事情。”,“我忘了自己应当谨慎从事”,“那把刀跟新的一样,精光锃亮,清清白白,一丝血迹都没有留下”。这些线索指引着你,一步步走向真相。
因为小说情节的跳脱,线索和暗示变得格外重要,你不知道博尔赫斯哪一句话别有用心,又发现似乎每一句话都恰到好处,线索藏在隐秘的角落,不经意间便匆匆错过了,待你第二次翻开,一字不漏的仔细揣测才突然间发现,原本不起眼的一句带过,才是寻找事件真相的关键所在。
因为缺失,所以渴望
在故事中,血性,勇猛是一种被承认并推崇的英雄品质,杀死雷亚尔的凶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替代了罗森多的位置,成了村里年轻人模仿的对象。
而博尔赫斯本人却并非如此,他性格腼腆甚至懦弱,一辈子都埋头在图书馆,沉迷于阅读。在与第一任妻子关系破裂之后他选择逃离家庭而不是承担责任。尽管内心对率性,热血有着无限憧憬,但性格上的极大反差使这成为他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
于是就有了《玫瑰色街角的汉子》,博尔赫斯将这种憧憬移入作品之中,让“我”这个崇拜着偶像的无名小卒一夜之间感受到了信念的崩塌,“我”愤怒了,“我”不甘成为河岸边的一株野草,“居住的地方越是卑微就越应该有出息。”于是“我”将刀刺入了雷亚尔的身体,杀掉他仿佛是“我”不再卑微的证明。
博尔赫斯确实成功了,他用大段的空缺,精妙的结构吊足了读者的胃口,在惊叹他严密逻辑的同时不得不承认其过人的把控力,和创造力,一个热血,率性的英雄梦在小说中得以实现。
毕竟“我”把马甲下的短刀拔了出来,杀死了懦弱,却依旧清清白白。
作为一位“作家们的作家”,博尔赫斯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对于很多作家来说,他像是一种资源般的存在。
“他,甚于任何其他人,大大创新了小说的语言,为整整一代伟大的拉美小说家开创了道路。”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
“来自旧世界,却有着未来派的眼界。”
——萨松·亨利
“博尔赫斯不仅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文学巨匠,而且还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创造大师。正是因为博尔赫斯,我们拉丁美洲文学才赢来了国际声誉。他打破了传统的束缚,把小说和散文推向了一个极为崇高的境界。”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博尔赫斯非常具有知识分子气质,他写的作品都很短小,也很精彩,涉及历史、哲学、人文等许多方面,我当然受过他的影响。
——保罗·奥斯特
“如果有哪一位同时代人在文学上称得起不朽,那个人必定是博尔赫斯。他是他那个时代和文化的产物,但是他却以一种神奇的方式知道如何超越他的时代和文化。他是最透明的也是最有艺术性的作家。对于其他作家来说,他一直是一种很好的资源。”
——苏珊·桑塔格
《玫瑰色街角的汉子》原文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既然问起已故的弗朗西斯科·雷亚尔,我就谈谈吧。这里不是他的地盘,他在北区瓜达卢佩湖和炮台一带比较吃得开,不过我认识他。我只跟他打过三次交道,三次都在同一个晚上,那晚的事我怎么都不会忘记,因为卢汉纳拉在我家过夜,罗森多·华雷斯离开了河镇,再也没有回来。你们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当然不会知道那个名字,不过打手罗森多·华雷斯是圣丽塔村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是玩刀子的好手,跟堂·尼古拉斯·帕雷德斯一起,帕雷德斯则是莫雷尔那一帮的。华雷斯逛妓院时总打扮得整整齐齐,一身深色的衣服,佩着银饰;男人和狗都尊敬他,女人们对他也另眼相看;谁都知道有两条人命坏在他手里;油光光的长头发上戴着一顶窄檐高帮呢帽;有人说他一帆风顺,给命运宠坏了。村里的年轻人模仿他的一举一动,连吐痰的架式也学他的。可是罗森多真有多少分量,那晚上叫我们掂着了。
说来仿佛离谱,然而那个大不寻常的夜晚是这么开头的:一辆红轱辘的出租马车挤满了人,沿着两旁是砖窑和荒地的巷子,在软泥地上颠簸驶来。两个穿黑衣服的人不停地弹看吉他,喧闹招摇,赶车的甩着鞭子,哄赶在白花马前乱窜的野狗,一个裹着斗篷的人不声不响坐在中间,他就是赫赫有名的牲口贩子弗朗西斯科·雷亚尔,这次来找人打架拼命。夜晚凉爽宜人;有两个人坐在马车揭开的皮篷顶上,好像乘坐一条海盗船似的。这只是一个头,还发生了许多事情,我们后来才知道。我们这些小伙子老早就聚在胡利亚舞厅里,那是高纳路和马尔多纳多河中间一个铁皮顶的大棚屋。门口那盏风化红灯的亮光和里面传出的喧哗,让人打老远就能辨出这个场所。胡利亚虽然不起眼,却很实惠,因为里面不缺乐师、好酒和带劲的舞伴。说到舞伴,谁都比不上卢汉纳拉,她是罗森多的女人。她已经去世了,先生,我多年没有再想她,不过当时她那副模样,那双眼睛,真叫人销魂。见了她,你晚上休想睡着。
烧酒、音乐、女人,承罗森多看得起才骂的一句脏话,在人群中使我受宠若惊的拍拍肩膀,这一切叫我十分快活。同我跳舞的那个女的很随和,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探戈舞任意摆布我们,使我们若即若离,一会儿把我们分开,一会儿又让我们身体贴着身体。男人们正这样如醉如痴、逍遥自在时,我蓦地觉得音乐更响了,原来是越来越行近的马车上的吉他声混杂了进来。接着,风向一转,吉他声飘向别处,我的注意力又回到自己和舞伴身上,回到舞厅里的谈话。过了一会儿,门口响起盛气凌人的敲门和叫喊声。紧接而来的是一片肃静,门给猛地撞开,那人进来了,模样跟他的声音一般蛮横。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他叫弗朗西斯科·雷亚尔,只见面前站着一个高大壮实的家伙,一身黑衣眼,肩上搭着一条栗色围巾。我记得他脸型像印第安人,满面愠色。
门给撞开时正好打在我身上。我心头无名火起,向他扑去,左手打他的脸,右手去掏那把插在马甲左腋窝下的锋利的刀子。可是这一架没有打起来。那人站稳脚,双臂一分,仿佛拨开一个碍事的东西似的,一下子就把我撂到一边。我踉跄几步,蹲在他背后,手还在衣服里面,握着那把没有用上的刀子。他照旧迈步向前走,比被他排开的众人中间随便哪一个都高大,对哪一个都没有正眼看一看。最前面的那批看热闹的意大利人像折扇打开那样赶快散开。这个场面并没有保持多久。英国佬已经在后面的人群中等着,那个不速之客的手还没有挨着他肩膀,他一巴掌就扇了过去。这一下大伙都来劲了。大厅有好几丈长,人们从一头到另一头推推搡搡,吹口哨,啐唾沫招惹他。最初用拳头,后来发现拳头挡不住他的去路,便叉开手指用巴掌,还嘲弄似的用围巾抽打他。这样做也是为了把他留给罗森多去收拾。罗森多在最里面,不声不响,背靠着墙,一直没有动静。他一口接着一口地抽烟,似乎早已明白我们后来才看清的事情。牲口贩子给推到他面前,脸上带着血迹,后面是一群吵吵嚷嚷的人,他不为所动。尽管人们吹口哨,揍他,朝他啐唾沫,他走到罗森多面前才开口。他瞅着罗森多,用手臂擦擦脸,说了下面一番话:
“我是弗朗西斯科·雷亚尔,北区来的。我是弗朗西斯科·雷亚尔,人们叫我牲口贩子。这些混小子对我动手动脚,我全没理会,因为我要找个男子汉。几个碎嘴子说这一带有个心狠手辣、会玩刀子的人,说他绰号叫打手。我是个无名之辈,不过也想会会他,讨教讨教这位好汉的能耐。”
他说话时眼睛一直盯着罗森多。说罢,右手从袖管里抽出一把亮晃晃的刀子。周围推推搡搡的人让出了地方,鸦雀无声,瞧着他们两人。甚至那个拉小提琴的瞎眼混血儿也转过脸,冲着他们所在的方向。
这时候,我听见背后有些动静,回头一看,门口有六七个人,准是牲口贩子带来压阵的,年纪最大的一个有点农民模样,皮肤黝黑,胡子花白;他刚上前,一看到这么多女人和这么亮的灯光,竟呆着不动了,甚至还恭敬地摘下了帽子。其余的人虎视眈眈,如果有不公平的情况马上就出头干预。
罗森多怎么啦,怎么还不教训教训那个气势汹汹的人?他还是一声不吭,眼睛都不抬。他嘴上的香烟不见了,不知是吐掉还是自己掉落的。他终于说了几句话,不过说得那么慢,大厅另一头根本听不清。弗朗西斯科·雷亚尔再次向他挑战,他再次拒绝。陌生人中间最年轻的那个吹了一声口哨。卢汉纳拉轻蔑地瞅着罗森多,头发往后一甩,排开女人们,朝她的男人走去,把手伸进他怀里,掏出刀子,退了鞘,交给他,说道:
“罗森多,我想你用得上它了。”
大厅屋顶下面有一扇宽窗,外面就是小河。罗森多双手接过刀,用手指试试刀刃,似乎从没有见过似的。他突然朝后一仰,扬手把刀子从窗口扔了出去,刀子掉进马尔多纳多河不见了。我身上一凉。
“宰了你还糟蹋我的刀子呢。”对方说着抬手要揍他。这时,卢汉纳拉奔过去,胳臂勾住他脖子,那双风骚的眼睛瞅着他,气愤地说:
“别理那家伙,以前我们还把他当成一条汉子呢。”
弗朗西斯科·雷亚尔愣了一下,接着把她搂住,再也不打算松手似的,他大声吩咐乐师们演奏探戈和米隆加舞曲,吩咐找快活的人都来跳舞,米隆加像野火一般从大厅一头燃到另一头。雷亚尔跳舞的神情十分严肃,但把舞伴搂得紧紧的,不留一点空隙,使她欲仙欲死。跳到门口时,雷亚尔嚷道:
“借光腾腾地方,她在我怀里睡着啦!”
说罢,他们两个脸贴着脸出去了,仿佛随着探戈的波涛迷迷糊糊地漂流。
我肯定恼羞得满脸通红。我跟舞伴转了几个圈子,突然撂下了她。我推说里面人多太热,顺着墙壁走到外面。夜色很美,但美景为谁而设?那辆出租马车停在巷子拐角的地方,两把吉他像两个人似的端端正正竖在座位上。他们这样大大咧咧扔下吉他真叫我心里有气,仿佛量我们连他们的吉他都不敢碰。想起我们自己无能,我直冒火。我一把抓起耳朵后面别着的石竹花,扔进水塘,望了许久,脑子里什么都不在想。我希望这一晚赶快过去,明天马上来到就好了。这当儿,有人用胳臂肘撞了我一下,几乎使我感到宽慰。是罗森多,他独自一个人出了镇。
“你这个混小子老是碍事。”他经过我身边时嘀咕说,我不知道他是拿我还是拿自己出气。他顺着比较幽暗的马尔多纳多河一边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我继续凝视着生活中的事物——没完没了的天空、底下独自流淌不息的小河、一匹在打瞌睡的马、泥地的巷子、砖窑——我想自己无非是长在河岸边的蛤蟆花和骷髅草中间的又一株野草罢了。那堆垃圾中间又能出什么人物?无非是我们这批窝囊废,嚷得很凶,可没有出息,老是受欺侮。接着我又想,不行,居住的地区越是微贱,就越应该有出息。垃圾?米隆加舞曲发了狂,屋里一片嘈杂,风中带来金银花的芳香。夜色很美,可是白搭。天上星外有星,瞅着头都发晕。我使劲说服自己这件事与我无关,可是罗森多的窝囊和那个陌生人的难以容忍的蛮横总是跟我纠缠不清。那个大个儿那晚居然弄到一个女人来陪他。我想,那一晚,还有许多夜晚,甚至所有的晚上,因为卢汉纳拉不是随便闹着玩的女人。老天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去不了太远,也许随便找一条沟,两个人已经干上了。
我终于回到大厅时,大伙还在跳舞。
我装着没事的样子混进人群,我发现我们中间少了一个人,北区来的人和其余的人在跳舞。没有推撞,有的只是提防和谨慎。音乐回肠荡气,没精打采,跟北区的人跳舞的女人一句话也不说。
我在期待,但不是期待后来出的事情。
我们听到外面有一个女人的哭声,然后是我们已经听到过的那个声音,这会儿很平静,几乎过于平静,以至不像是人的嗓音。那声音对女人说:
“进去,我的姑娘。”又是一声哭叫。接着,那个声音似乎不耐烦了。
“我让你开门,臭婆娘,开门;老母狗!”这时候,那扇摇摇晃晃的门给推开了,进来的只有卢汉纳拉一个人。她不是自动进来的,是给赶进来的,好像后面有人在撵她。
“有鬼魂在后面撵。”英国佬说。
“一个死人在撵,朋友。”牲口贩子接口说。他的模样像是喝醉了酒。他一进门,我们便像先前那样腾出了地方,他摇摇晃晃迈了几步——高大的身材,视而不见的神情——像电线杆似的一下子倒了下去。同他一起来的那伙人中间有一人把他翻过来,让他仰面躺着,再把斗篷卷成一团,垫在他脑袋下面。这么一折腾,斗篷染上了血迹。我们这才看到,他胸口有一处很深的伤口;一条猩红色的腰带,当初给马甲遮住,我没有发现,现在被涌出来的血染黑了。一个女人拿来白酒和几块在火上燎过的布片准备包扎。那男人无意说话。卢汉纳拉垂下双手,失魂落魄地望着他。大伙都露出询问的神情,她终于开口了。她说,她跟牲口贩子出去之后,到了一片野地上,突然来了一个不认识的男人,非找他打架不可,结果捅了他一刀,她发誓说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反正不是罗森多。可谁会信她的话?
我们脚下的人快死了。我想,捅他的人手腕子够硬的。不过脚下的人也是条硬汉。他进门时,胡利亚正在喝马黛茶①,茶罐传了一巡,又回到我手里,他还没有咽气。“替我把脸蒙上,”他再也支持不住了,便缓缓地说。他死在眉睫,傲气未消,不愿意让人看到他临终时的惨状。有人把那顶高帮黑呢帽盖在他脸上,他没有发出呻吟,在呢帽下面断了气。当他的胸膛不再起伏时,人们鼓起勇气取下帽子。他脸上是死人通常都有的倦怠神情,当时从炮台到南区的最勇敢的人共有的神情;我一发现他无声无息地死了,对他的憎恨也就烟消云散。
①马黛茶,南美饮料,饮用时在梨形茶罐内插一小管吮吸。
“活人总有一死。”人群中间一个女人说,另一个也若有所思地找补了一句:
“再了不起的人到头来还不是招苍蝇。”
这时候,北区来的人悄悄地在说什么,之后有两人同时高声说:
“是那女人杀死的。”
一个人朝她嚷嚷说是她杀的,大家围住了她。我忘了自己应当谨慎从事,飞快地挤了进去。我一时情急,几乎要拔刀子。我觉得如果不是所有的人,至少有许多人在瞅我。我带着讥刺的口气说:
“你们大伙看看这个女人的手,难道她有这份气力和狠心捅刀子吗?”
我若无其事地又说:
“据说死者是他那个地区的一霸,谁想到他下场这么惨,会死在这样一个平静无事的地方?我们这里本来太太平平,谁想到来了外人找麻烦,结果捅出这么大的乱子?”
鞭子自己是不会抽打的。
这当儿,荒野上逐渐响起了马蹄声,是警察。谁都明哲保身,不愿意找麻烦,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尸体扔进河里。你们还记得先前扔出刀子的那扇宽窗吧。黑衣服的人后来也是从这里给扔出去的。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抬起来,身上一些钱币和零星杂物全给掏光,有人捋不下戒指,干脆把他的手指也剁了下来。先生们,一个男子汉被另一个更剽悍的男子汉杀死之后,毫无自卫能力,只能听任爱占小便宜的人摆弄,扑通一声,混浊翻腾、忍辱负重的河水便把他带走了。人们收拾尸体时,我觉得不看为妙,因此不知道是不是掏空了他的脏腑,免得他浮出水面。那个花白胡子的人一直盯着我。卢汉纳拉趁着混乱之际溜出去了。
维护法律的人来查看时,大伙跳舞正在劲头上。拉小提琴的瞎子会演奏几支如今不大听到的哈瓦那舞曲。外面天快亮了。小山风上的几根木桩稀稀落落的,因为铁丝太细,天色这么早,还看不清。
我家离这里有三个街区,我悠闲地溜达回去。窗口有一盏灯光,我刚走近就熄灭了。我明白过来之后,立刻加紧了脚步。我又把插在马甲左腋窝下的那把锋利的短刀抽出来,端详了一番,那把刀跟新的一样,精光锃亮,清清白白,一丝血迹都没有留下。
(王永年 译)
马黛树是冬青科常绿灌木,只有在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等国家才有生长,在南美洲马黛树的叶子被当地人用来泡饮,具有均衡营养的作用。由于马黛茶在南美洲的普遍被认可,阿根廷把马黛茶作为本国的四大国宝之一,南美人民称马黛茶为“南美仙草”。
据说 ,马黛茶 与 咖啡 、红茶 ,为世界上的“三大茶饮料” ,只听说过 ,但是没喝过 。
感谢你的提问,我也长知识啦 。
以上复制于《》 ,仅供参考 。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品搜搜测评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