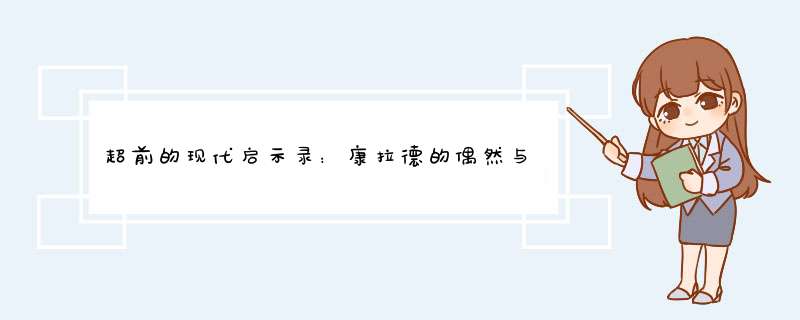
文/宝木笑
1979年大导演科波拉和马龙•白兰度、马丁•辛、罗伯特•杜瓦等一干明星一起拍了一部叫做《现代启示录》的片子,这部片子以越战为背景,表现手法隐晦,但内涵却非常深刻,直到今天仍然让很多影迷着迷。如今“现代启示录”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不但直指美国的越战泥潭,更代表着一种全球化浪潮下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崩塌。当年还有这样一段插曲,好莱坞金牌编剧米利厄斯在准备写《现代启示录》剧本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改编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然而由于版权的原因最终无果。米利厄斯并没有放弃,他将《黑暗的心》作为《现代启示录》的主题寓言,重新写了一个故事,精神内核依然是《黑暗的心》,最终获得成功。
如今回想,如果《现代启示录》可以作为一种全球化反思的标签,那么英国著名作家约瑟夫•康拉德似乎很有些“先知”的味道。所以,马娅•亚桑诺夫在其康拉德传记《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约瑟夫•康拉德》中,这样描述自己在阅读康拉德作品中的感受:“《黑暗的心》只是刚刚开始,当我继续阅读康拉德更多的作品时,常常会惊叹他那种‘看待世界的特有方式’竟然如同先知般得到了一一应验”。康拉德的这种超越性也成就了这位哈佛大学的历史教授,《守候黎明》拿到了2018年度全球历史类图书最重要奖项之一坎迪尔奖,还记得6年前的大奖作品,就是如今在国内依然很火热的裴士锋的《天国之秋》。
为了这本传记,这位哈佛女教授不惜只身前往局势十分动荡的刚果。按照马娅•亚桑诺夫的说法,她非常想体验康拉德百年前的传奇之旅。确实,康拉德对于时代和文明的超前思维并不是产生于书斋的哲思,事实恰恰相反,康拉德仿佛是一名“雾都孤儿”,他的人生充满着一种坚韧的偶然,那是各种创伤累积而成的“传奇”。1857年12月,康拉德出生在沙俄统治之下的波兰,《守候黎明》对此不惜进行了大篇幅考证。康拉德本名为肯拉德,确为波兰贵族“什拉赫塔”的直系后裔。马娅•亚桑诺夫在全书开始,便在使用一种全球化的笔法述说全球化的康拉德。开篇的“没有家、没有国”,除了点明康拉德幼时悲剧的布景,更在于隐晦地指出了全球化的最终走向——人类将模糊疆界概念,文明将在碰撞中重组,个人命运将充满偶然与必然的融合。
就像康拉德,如果不是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的历史风潮,他可能会永远生活在波兰,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成长为一位风度翩翩的贵族青年。然而,世界在距今百年之前虽未有全球化之名,却已有了全球化之实,而康拉德家族和整个波兰所面临的正是这种全球化带来的悲剧。康拉德的家族在波兰享有令人尊敬的地位,其祖父是拿破仑战争时代的老兵,曾经自费招募骑士团抗击俄国人,而康拉德的父母都是积极的抵抗运动参与者。最终,康拉德的父母被俄国当局流放致死,体弱多病的小康拉德被送回外婆和舅舅家寄养。那是一个整个世界的边界都在被打破的时代,个人的漂泊成为一种必然。康拉德16岁时又只身闯荡法国,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航海生涯,其间在申请法国国籍未果之后,康拉德加入了英国商船队,从普通船员一直做到船长,并最终获得了英国国籍。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化并非一定是一个褒义词,它充其量应该是一个中性词,代表的仅仅是一种趋势——国家、民族、文化、技术、艺术等在这个趋势中相互撞击,可能会出现好的事情,当然也会发生很多坏的事情。康拉德的时代和他自己的经历,显然正是对这种情况的最佳解释。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用马娅•亚桑诺夫的话说就是“那个世界就是由那些‘远在天边的无名之地’和‘近在眼前的有名之地’而构成的,康拉德的人生,以及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便是‘无名之地’和‘有名之地’遭遇碰撞的故事”。而康拉德作为文学家的身份,很大程度上是这种碰撞之后水到渠成的必然,他的小说多基于丰富的个人经历,是他在足迹遍布欧、亚、非、拉美以及其间大洋之后的艺术再造。康拉德个人经历的优势,使其尤为擅长海洋冒险小说,被誉为“海洋小说大师”,在其生前就获得极大成功(虽然这成功在他自己看来来的有些晚),并拉开了与吉卜林、史蒂文森等同时代“新浪漫主义”小说家的距离。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守候黎明》在康拉德的精神世界里继续前行,并最终抓住了康拉德对于今日世界最为核心的现实意义——他超前的全球化思维。《黑暗的心》至今仍然是最受广泛阅读的英语小说之一,这部小说与《吉姆爷》、《间谍》、《胜利》等在内的13部长篇、28篇短篇和2篇回忆录一起构建了康拉德的文学世界,也是他的思想殿堂。康拉德的全球化思维最直接的表象就在于,在这种思维下,他没有像其他伟大作家那样构建一个相对固定的故事地点,比如鲁迅先生的鲁镇、莫言先生的高密。康拉德将他的文学世界置于极为广阔的地理空间跨度内,从欧洲到亚非拉各洲、从都市中心到偏远村镇、从灯红酒绿的城市到广袤原始的旷野、从繁华喧闹的陆地到一望无际的海洋……他的小说也大多承载着更为深沉的时代和命运主题,比如非洲与欧洲、文明与野蛮、个人与命运以及帝国主义、种族灭绝、心智癫狂、人性深处等。
更为重要的是,康拉德这种充满现代启示录意义的沉思,无处不在张扬着先知一般的超前。康拉德在长久的航海生涯中,在深入英帝国的海外拓展中,在一生的世界漂泊中,探讨着全球化世界下的生活分支,比如角色错位所引起的道德和物质影响、多族群社会的紧张态势和机遇、科技更新所导致的变迁与破坏,而这些对今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9•11”之后,西方世界与阿拉伯世界的矛盾变得激烈而更加血腥,这不由让人们想起康拉德在1907年的《间谍》中,就已经描述了伦敦恐怖主义爆炸的图谋。2008年金融危机让抗议全球化的浪潮前所未有,而康拉德在1904年的《诺斯特罗莫》中,已经在探讨跨国集团那些对赌的鬼把戏。当我们在新世纪的第一个二十年开始反思技术对于人类的反噬,当赛博朋克重新引起我们的重视,当基因改造和伦理危机前些天还在挑战着我们的神经,康拉德在百年前的《吉姆爷》中就已经开始讲述技术对于人类传统的毁灭,以及人类内心良知在这种毁灭中的焦灼。难怪奈保尔曾经不无嫉妒地抱怨:康拉德怎么会如此鬼使神差般“步步抢我之先”,如何就能够在一百多年前就“思索我今日所识的世界”。
实际上,就像康拉德很不喜欢被贴上什么“海洋文学大师”的标签一样,康拉德也许会将这种被人赞叹的超前性,举重若轻地归结为自己命运的偶然。这位全名为约瑟夫•特奥多尔•肯拉德•科尔泽尼奥夫斯基(康拉德为后来自己所改)的船长,写作一开始只是他的业余爱好,就像如今很多朋友喜欢在网络上码字一样。甚至康拉德二十世纪最佳英语作家的名头也来的非常偶然,要知道讲着波兰语和法语长大的康拉德,直到21岁才开始学习英语,也许当年心境的稍微改变就会使康拉德选择完全不同的道路。并且,康拉德的外婆和舅舅家的条件依然不错,家人在很多年里是反对他选择水手工作的。而康拉德在经济拮据的前半生,为了自食其力,更在意的是如何还上外债和活下去,他找了很多工作,也换了很多工作,但从未想过去做全职作家。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什么康拉德在这种种偶然中成为了必然的康拉德。我们不妨先从康拉德的人生轨迹说起,貌似波兰贵族康拉德是在数次偶然中辗转到了法国,最终漂泊到了伦敦。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当时波兰在俄国的重压之下,国内很多人都在逃往西欧,那已经成为了一股潮流。至于康拉德一生对于英国的难舍情结,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并不难理解,“日不落帝国”虽然面临着各种危机,但不得不承认在当时的世界,“在世界的每一寸海面上,英国商船队均是漂浮着的最强商业力量”。在康拉德成长的19世纪60年代,英姿飒爽的航海生涯既符合当时全球化的拓张需求,其背后的冒险和探索精神,更符合19世纪后半叶的欧美心态——19世纪是人类技术和认知发展极为迅速的时代。因此,无论是作为当时被沙俄迫害的波兰贵族的后裔,还是作为一个向往西欧的东欧年轻人,康拉德选择出海,选择英国,都是当时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是一种时代的必然。
就此而言,康拉德种种偶然背后的必然,其实是一种时代对于个体的反作用。但我们还必须从更深的角度挖掘,找出康拉德的思想成为一种充满超越感的现代启示录的原因。从最直接的原因来看,当时英语世界的作家绝大部分虽然向往着全球化的世界,但却没有像康拉德这样亲身用20年的时间,去感受那个全球化的世界——康拉德不但深入非洲刚果,更远赴澳大利亚,还在东南亚逗留了不短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康拉德的这种感受又绝非什么田野调查一类的环球旅行,他从最艰苦、最贫穷的最低级水手做起,和非洲的奴隶、亚洲的仆役、欧洲的酒鬼等最底层人群活在一起。而后来康德拉又一步步成长为大型蒸汽轮船的船长,又有机会结识政府要员、跨国公司经理、殖民地军官、土著部落首领等一系列高层,又能够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反过来思考自己当年在底层见到的一切。这样多维的样本比对和随之而来的深刻思索,并不是每个作家都能有的经历。
如果进一步来看康拉德这种偶然与必然交织的人生,我们又会发现更多宿命一般的内涵,而这逐渐让康拉德最终实现了思想的超越。康拉德从上世纪开始,一直就是文艺批评界的“显学”,他的作品不但空间跨度惊人,而且涉及到道德良知、伤痕心理、政治困境、叙事变革、文化解构、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等文艺批评界几乎所有最关注的范畴。康拉德的身世注定让他对时代的宏观之力有更多感触,《守候黎明》描述了他的童年是如何目睹了父母的离世,特别是父亲作为一位爱国诗人是如何遭受致命的打击。所以,终其一生,康拉德都从未忘记或原谅摧残他童年的“大俄罗斯帝国压迫的阴霾”,也从未忘记过那种个体在宏大时代面前,特别是在全球化面前的渺小感和无力感。当这一切遇到康拉德日后的航海经历,当康拉德看到刚果黑奴是如何被严酷地压榨和残忍地杀害,当康拉德看到东南亚的生丝小厂无论如何努力工作都无法摆脱破产的命运,当康拉德看到欧洲的殖民者在肆意贬低其他文明并摧毁它们……康拉德内心中被激发出一种对于宏大历史和全球化裹挟的深深沉思,同时在感性上让康拉德在内心深处升起了一种深深的宿命感:“世界如同一个王国,无论你多么执着地要自行其是,但都无法摆脱命运的轨道”。
正因此,康拉德从来不会给他的小说加上任何“光明的尾巴”。在康拉德的小说中,人物常常会面对种种人生的关键抉择,但却没有什么令人激动的“反转”。在康拉德看来,承认历史的必然是一名小说家的本分,你可以“欺骗命运”,也可以把过往尘封,你可以随船共沉,也可以跳上救生艇逃亡,但不管怎样,你还是会无法摆脱一个时代的大势带给你的一切。在那个最早具备全球化雏形的时代,英帝国诞生了两位极为重要的作家――吉卜林和康拉德,他们都亲眼目睹、亲身经历过殖民强国在海外的所作所为,但他们最终的思考却截然不同。吉卜林无限推崇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意识,处处显示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优越性,作品中充满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和高人一等的权力意志。而康拉德的作品相比而言很不讨喜,虽然他依然对英帝国十分忠诚,但却仿佛一个倔强的中年大叔,偏偏喜欢拧着一股劲儿,说些歌功颂德之外的话,想一些纸醉金迷之外的事,写一些与众不同的文。
但是,时间会说明一切,就像康拉德超前的现代启示录已然在今天应验。只是我们在感慨康拉德作品和思想的同时,总是不自觉地会有些叹息,在他的身上仿佛看到了更多的东西。康拉德一生都在努力融入当时的“主流”,为此不惜吃很多苦,受很多委屈。比如,前面我们说康拉德21岁才开始学英语,而在他开始写作的时候已经30多岁了,这个年龄在当时那个时代已经算是很晚了,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更不用说当时英国文坛的冷嘲热讽,康拉德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英语教育,他的英语带有明显的外国腔调,吉卜林就曾非常不客气地评论康拉德的英语小说《“水仙号”的黑水手》读起来“更像是俄国小说而不是英国小说”,堪称“绝佳的外国作家的译作”。
虽然,这对于当时全球化的世界大势来说,简直是一件轻如鸿毛、绝对不值一提的小事,然而,如果我们细细品味,不难从中感觉到一丝似曾相识。其实,全球化包含的层面非常复杂,比如我们现在面对的城乡二元对立等问题,其实也是这个层面体系的题中之义……但无论如何,即使康拉德的一生都在承受着异质文化隔膜所带来的孤独感,他却依然故我。他坚信那些伤害是个体宿命的必然,他所要做的就是“使小说能够成为对人类经历更为真实可靠的记录载体”,他凭此深深凝望着文明得到的红利和受到的伤害,默默思索着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当古老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规则被动摇,新的一切还尚未订立,我们自己应当如何自处。而这种全球化视野中的理智和执着,则造就了康拉德偶然与必然交织的传奇人生。
“1857年圣诞节前三周……康拉德出生在一个小镇里,关于那座镇子,波兰有句老话,当你对某人说‘请寄一封信到别尔季切夫’,那么你的意思就是‘寄信到天涯海角’……正当他降临人世时,俄亥俄州某家银行的破产引发了一场金融危机,导致远在汉堡的许多公司被迫关门;英国军队正竭力镇压印度的一场叛乱;印度的军队开船至广东威胁中华帝国的官员;在欧洲人统治下的某个马来国家,华人侨民于婆罗洲的某条河岸揭竿而起;欧洲的服装和枪支在刚果盆地被那些从未见过白人的村民们用象牙来高价换取;某个美国兵痞被驱逐出了尼加拉瓜;美国制造的蒸汽轮船在南美洲的河流里破浪前进;在利兹生产的火车头拉动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首列火车……”
——《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约瑟夫•康拉德》
—END—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品搜搜测评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