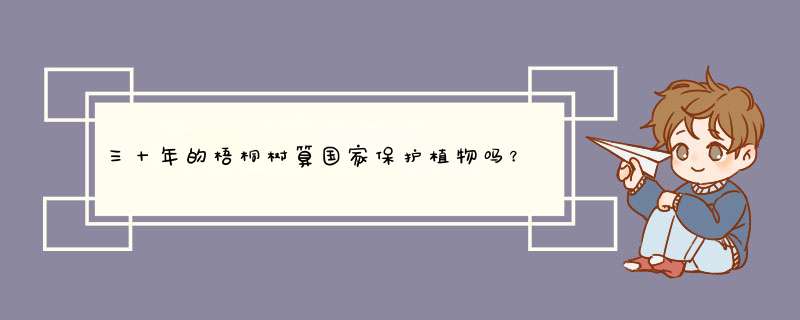
不是国家保护植物也是需要我们保护的。
梧桐树也叫凤凰树,取“家有梧桐树,引来金凤凰”之意,寄托着人们的美好愿望。
“中国梧桐”是梧桐科梧桐属的植物、别名青桐、桐麻 ,也属落叶大乔木,高达15米;树干挺直,树皮绿色,平滑。原产中国,南北各省都有栽培。梧桐生长快,木材适合制造乐器,树皮可用于造纸和绳索,种子可以食用或榨油,由于其树干光滑,叶大优美,是一种著名的观赏树种。中国古代传说凤凰“非梧桐不栖”。许多传说中的古琴都是用梧桐木制造的,梧桐对于中国文化有重要的作用。
梧桐树在古诗词中常有以下几种意像及寓意。
1、梧桐树象征高洁品格的意象及寓意
梧桐在古诗中有象征高洁美好品格之意。如“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诗经·大雅·卷阿》),诗人在这里用凤凰和鸣,歌声飘飞山岗;梧桐疯长,身披灿烂朝阳来象征品格的高洁美好。再如“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虞世南《蝉》),这首托物寓意的小诗,以高大挺拔,绿叶疏朗的梧桐为蝉的栖身之处,写出了蝉的高洁,暗喻自己品格的美好。庄子在《秋水》中也说:“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 鹓鶵是古书上说的凤凰一类的鸟。它生在南海,而要飞到北海,只有梧桐才是它的栖身之处。这里的梧桐也是高洁的象征。因此,古代有“栽桐引凤”之说。
2、 梧桐树象征忠贞爱情的意象及寓意
梧桐枝干挺拔,根深叶茂,在诗人的笔下,它又成了忠贞爱情的象征。如“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孔雀东南飞》),诗中用松柏梧桐的枝叶覆盖相交,象征了刘兰芝和焦仲卿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这双对纯真爱情的追求,对封建礼教的抗争的夫妻,生前被迫分离,死后合葬九泉,能不震撼人心?
3、 梧桐树象征孤独忧愁的意象及寓意
风吹落叶,雨滴梧桐,凄清景象,梧桐又成了文人笔下孤独忧愁的意象。如“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李煜《相见欢》),极形象生动地写出了这位亡国之君幽居在一座寂寞深院里的落魄相。重门深锁,顾影徘徊,只有清冷的月光从梧桐枝叶的缝隙中洒下来,好不凄凉!过去是居万民之上的君主,而今已成阶下囚,万千愁绪,满腔幽愤,尽在其中。亡国之恨何时了?又如“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徐再思《水仙子·夜雨》),深秋孤夜,夜雨滴打着梧桐和芭蕉,每一声都引起相思之人的阵阵秋思和缕缕愁绪。这既是一首雨夜相思曲,又是一幅凄风苦雨的秋夜图!面对此景,相思之苦便从词人心底涌起。作者对雨打梧桐和芭蕉的描绘,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凄婉惶惑,意境深远。
这个但愿对你有用
苏舜(香港诗人王伟明):从你的诗作中,我感觉到你受外国诗人的影响较深,如洛尔迦(Lorca)、惠特曼(Whitman)等。你喜欢这些外国诗人吗?是通过翻译来念他们的作品吗?
顾城:我外文不行,所以只能通过翻译来读外国诗。我爱人懂点英文,我俩有时也学着译点儿诗,这对我理解外国诗人的作品很有帮助。
确如你所说的,我受外国诗人的影响较深。我喜欢但丁、惠特曼、泰戈尔、埃利蒂斯、帕斯。其中最喜欢的还是洛尔迦和惠特曼。有一段我天天读他们的诗,把他们的诗带到梦里去,有些诗是一生读不尽的。
我喜欢外国诗有一个过程,很小的时候我就读普希金的童话诗《小飞马》。那时我不关心什么是诗,只想多知道些故事,另外再多翻到几页彩色插图。我发现惠特曼时笑了半天,我想他可真会胡言乱语。
认真开始读外国诗是在十多年后,我先读了些浪漫派的诗,感触不深,我觉得他们有些姿态是作出来的。真正使我震惊的是西班牙和它的那个语系的文学——洛尔迦、阿尔贝蒂、阿莱桑德雷、聂鲁达。他们的声音里有一种白金和乌木的气概,一种混血的热情,一种绝对精神,这声音震动了我。
我喜欢西班牙文学,喜欢洛尔迦,喜欢他诗中的安达露西亚,转着风旗的村庄,月亮和沙土。他的谣曲写得非常动人,他写哑孩子在露水中寻找他的声音,写得纯美之极。我喜欢洛尔迹,因为他的纯粹。
惠特曼和洛尔迦很不相同,他是开放型的,是广大博爱的诗人,他无所不在,所以不会在狭窄的道路上与人决斗。他怪样地看着人类,轻微地诅咒而更加巨大地爱着人类。他的诅咒和热爱如同阳光。对于他——惠特曼来说,对于他干草一样蓬松的胡须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解的,没有年龄,没有什么千万年的存在之谜。那些谜轻巧地像纸团,像移动杯子一样简单——灵魂和肉体是同一的,战绩和琐事、田野和人、步枪子弹和上帝是同一的,生和死是同一的,都是从本体上生长出来的草叶。
惠特曼是个超验的人,他直接到达了本体,到达了那种“哲学不愿超过、也不能超过的境界”。他留给人类的不是一本诗,而是一个燃烧着无尽核能的爱的太阳。我读惠特曼的诗很早,感应却很晚。我是个密封的人。一直到八三年的一个早上,痛苦的电流才熔化了那些铅皮,我才感到了那个更为巨大的本体——惠特曼。他的声音垂直从空中落下,敲击着我,敲击着我的每时每刻。一百年是不存在的,太平洋是不存在的,只有他——那个可望不可及的我,只有他——那个临近的清晰的永恒。我被震倒了,几乎想丢开自己,丢开那个在意象玻璃上磨花的工作。我被震动着,躺着,像琴箱上的木板。整整一天,我听着雨水滴落的声音。
苏舜:除了外国诗人的作品,你喜欢哪些中国诗人的作品,你喜欢中国古诗吗?请你谈谈对传统的看法。
顾城:我喜欢古诗、刻满花纹的古建筑,殷商时代的铜器;我喜欢屈原、李白、李贺、李煜,喜欢《庄子》的气度、《三国》的恢宏无情、《红楼梦》中恍若隔世的泪水人生。我就活在这样的空气里,我不仅喜欢读古诗,而且喜欢摹一些画送给朋友;我不仅喜欢古诗,而且喜欢在落叶中走,去默想它们那种魂天归一的境界;我常闭起眼睛,好像面对着十个太阳,让他们晒热我的血液。那风始终吹着——在萧萧落木中,在我的呼吸里,那横贯先秦、西汉、魏晋、唐宋的万里诗风;那风始终吹着,我常常变换位置来感知他们。
苏舜:你认为大诗人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顾城:我认为大诗人首先要具备的条件是灵魂,一个永远醒着微笑而痛苦的灵魂,一个注视着酒杯、万物的反光和自身的灵魂,一个在河岸上注视着血液、思想、情感的灵魂,一片为爱驱动、光的灵魂,在一层又一层物象的幻影中前进。
人类的电流都聚集在他身上,使他永远临近那个聚变、那个可能的工作,用一个词把生命从有限中释放出来,趋向无限。使生命永远自由地生活在它主宰的万物之中。他具有造物的力量。
最后,我想还有些纯客观的条件不仅对于大诗人,而且对于小诗人也适用,就是要有食物、要有安静的空间和时间来进行他们的工作。
苏舜:你曾随父亲下放到农村去,深为大自然所影响,故你早期的诗,主题多取材于大自然。现在你回到城市,你写的诗是否也发生了变化?
顾城;是的,是有很大变化。我习惯了农村,习惯了那个粘土作成的小村子,周围是大地,像轮盘一样转动。我习惯了,我是在那里塑造成型的。我习惯了一个人向东方走、向东南方走、向西方走,我习惯了一个人随意走向任何方向。候鸟在我的头顶鸣叫、大雁在河岸上睡去,我可以想象道路,可以直接面对着太阳、风,面对着海湾一样干净的颜色。
在城里就不能这样。城里的路是规定好的,城里的一切都是规定好的。城里有许多好东西,有食物,博物馆、书,有信息,可就是没有那种感觉,没有大平原棕色的注视,没有气流变幻的《生命幻想曲》。城里人很注意别人的看法,常用时装把自己包裹起来。
我不习惯城市,可是我在其中生活着,并且写作。有时一面面墙不可避免地挤进我的诗里,使我变得沉重起来。我不能回避那些含光的小盒子和溶化古老人类的坩埚,我只有负载着他们前进,希望尽快能走出去。我很累的时候,眼前就出现了河岸的幻影、我少年时代放猪的河岸。我老在想港口不远了,我会把一切放在船上。
大凡诗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这是他梦中的伊甸园,是他超越世俗,用诗的语言拼砌成的彼岸圣地。然而诗人不免要生活在此岸之中,他同时又是一个凡夫俗子,人所具有的他皆具有。就在两个世界之间,诗人保持着灵与肉,价值与功利,审美与理性的微妙平衡。唯独顾城 ,在他的人格之中只有一重世界,那就是目孩提起他大脑袋里面所装的自我迷恋的形而上世界。顾城称自己是“被幻想妈妈宠坏的任性孩子”。他早熟,当别的孩子还是拖着鼻涕、懵然无知的年龄,他已经 开始了用诗构筑自己的童话王国。但他又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用舒婷的话说“是一个不肯长大的孩子”,只相信自己编织的童话。孩童的意识里自我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是同一个空间,世界应当如他所想象的那般单纯美丽,或者说,我就是整个世界。顾城也相信自己的心灵与天地万物的同一:"我们相信习惯的眼睛,我们视而不见,我们常常忘记要用心去观看,去注视那些只有心灵才能看到的本体。日日、月月、年年,不管你看到没有,那个你,那个人类的你都在运行,都在和那些伟大的星宿一起烧灼着宇宙的暗夜。"他甚至坚信,诗人应该像上帝一样,“具有造物的力量”。
拒绝长大的诗人所愿意面对的是那个诗境中天地万物与我同一的世界,他只有自我放逐,将自己与世俗世界隔离,不仅遁世,连自己的身体都感到讨厌,最好不食人间烟火,全身心地逃避于抽象的彼岸世界。可以这样说,顾城的肉体对他来说已经不存在或不愿存在,他只为他的精神而活着,为那些整日折磨着他的奇奇怪怪的念头活着。
在朦胧诗人里面,北岛是愤世嫉俗的;舒婷充满了生命的情趣;而顾城却是反社会的,他怀疑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必要和可能,他怀疑语言的可靠性和真实性,甚至拒绝对这个地无奈生存其间的世俗社会承担一切义务和责任。像所有的乌托邦理想主义者一样,他对现代化的大都市充满了厌恶之情,认定一切按部就班的城市缺乏生命的活力。他相信“在我的诗中,城市将消失,最后出现的是一片牧场”。最后顾城果然远离城市,远离人群,在偏僻的小岛上开垦自己的伊甸园,伴着晨露,伴着鸟语,也伴着乌托邦的幻想。
顾城那著名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个中的“黑夜”大约指的还是世俗的昏暗,诗人欲以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去拥抱一个"光明"的彼岸世界。如果仅仅到这里为止,诗人的确意义非凡,在我们这个物欲过于泛滥,凡夫俗子主宰人类,世人普遍丧失超验精神的地球上,顾城以自己童话般的梦想震憾了每一颗不甘沉沦于俗世的心灵,他那陶渊明式的现代田园生活也令每一个留恋大自然的都市中人羡慕不已。
王晓玉在《我为谢烨一哭》中写道:“从她遭到那要命的一斧头,到还剩一口气被人发现,再到一个半小时后不治身亡,她大不幸地苟延残喘了许久。死,已非她所愿;苟延残喘,更使她非但不得不细细领受肉体上的折磨,而且要加倍地品味那因为临死前的大彻大悟而不能不正视的事实所带给她的的心灵上的痛苦。”
(5)谢烨已离世人远去,我们已无法猜度死者弥留时的心思。也许如王晓玉所说的梦醒之后晚到的彻悟,也许她依然在梦中,为终于殉了那份理想而自慰。暂且撇开价值评价,从人道角度出发,我宁愿是后者,这样也可以多少减轻死者临终前的痛楚。
这是中国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尽管是以那样一种极端的形式演给我们看。在今天这样一个物欲横行,精神失落的时代里,它的意味是异常复杂的。我们需要精神的马托邦,以显示人类文明自我批判和超越精神的永恒价值。但我们又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避免将这种精神的乌托邦直接还原为现实,以诗意的世界去整合世俗的世界。诗意与残忍,仅仅只有一步之遥,类似的马托邦悲剧我们已经看到得太多太多:法国的大革命、中国的“文革”、美国的“人民圣殿教”……这次不过是在一个孤独的小岛上,一个孤独的诗人那里重演了一遍而已。悲剧的语境不一,角色不同,但性质却总那么似曾相识。
诗的魅力是永恒的,但万万离不得这个远不美好的俗世。
顾城的情敌刘湛秋醉说当年情
据《蜀报》陈蕙如报道:都说诗人都是不甘寂寞的,诗人刘湛秋便是如此。他屡屡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人物:他和杀妻自缢的诗人顾城拥有同一个情人--英儿(李英,笔名麦琪);他开车无意撞残一名大提琴手,被对方索赔49万元,这场官司12月底将见分晓。12月5日午后,记者采访刘湛秋时,饭后的他有点微醉,为数不多的乱发仍然很张扬地显示着主人的个性。当记者试探地提及他和英儿的往事时,刘湛秋一点也不回避,“让人刻骨铭心的感情呵!”他说,在和刘湛秋的谈话中,他的激情、敏锐、坦诚无时无刻不提醒听者,这是一个纯粹男人的真言。
在英儿认识顾城之前,她和刘湛秋就已经难舍难分了。“当时我不知道有顾城这个人,后来我最不提防的人也是他。我告诉英儿,你一个人去新西兰,到顾城那儿我最放心。”“为什么呢?”记者好奇地问。“顾城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不近女色的人,对我丝毫不构成竞争力。”“是你的轻视使你把自己的女人送入他人的怀抱吗?”刘湛秋笑而不答,“任何男人对女人都有渴望,包括最没有渴望的顾城。”“顾城抢走英儿,靠的是什么?”记者“步步紧逼”。“靠一种软弱,他的弱者形象让毫无心计的英儿无法拒绝。”
随着谈话的深入,刘湛秋的回答更加坦白。“这段感情毫无疑问会伤害另一个女人吧?”“我的前妻是个很好的女人。”他欲言又止,“我这一生对不起一个女人,但不知道该对不起谁。”“有没有想过重新组建家庭?”“我对结婚有恐惧感。”刘湛秋摇摇头,或许他在想,相依相伴一生的人已经被自己弄丢了吧。
刘湛秋不只一次地告诉记者:男人的魅力在于勇气。这个六十多岁的可爱老头儿却一次次地像孩子似的迷恋于36岁的英儿的怀抱。“她的善解人意让我感动。”说这话时,刘湛秋不禁望向窗外,眼中带着憧憬。“那你怀念这段感情吗?”“ 不,不,不说怀念,她今年从澳大利亚回来看我,我们一如当初。”这时候,冬日的一抹阳光静静地斜照在刘湛秋酒醉微醺的脸上。“人生就是这样啊,说没有就没有了。”他突然说。(1999年12月22日 华声报)
顾城和诗 / 顾工
“爸爸,爸爸,我又想出来一首诗……”8岁的儿子顾城,每天从西直门小学放学回家,就沿着曲曲折折的楼梯、长长的南道奔跑着,推开房门扑到我的面前。小小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他大喘着气把他的诗背给我听——是塔松和丽珠的故事;是云朵和土地的对话;是瓢虫和蚂蚁的私语……
我凝视着他深藏梦幻的瞳仁,时惊时喜时忧——8岁的瞳仁中也有忧患吗?是小白兔似的忧愁,还是小松鼠似的忧虑?……他背诵完他的“诗”,也常常凝视,凝视在雨云下忙于搬家的蚂蚁;在护城河里游动的蝌蚪和鱼苗;在屋檐下筑窝的燕子……“文革”初期,有人在我们楼窗下马路对面的墙上,刷了条大标语,不知是贴反了,还是贴措了,马上被众多的路人围拢来,死死地缠住,揪住,按下头,用脚踢……顾城起初是从窗扇的缝隙向外看,后来他恐惧了,脸色惨白,再不向窗外多看一眼,他越来越想躲开纷争,躲开喧嚣的激越的声音,只想去那只有天籁的世界。
有这样的世界吗?当一辆卡车把我们抄家后的家具,连人一同载走的时候,在12岁的小顾城眼里,流露着迷惘也流露着喜悦——我们全家是不是正在迁移,迁移到一个天籁世界?!渤海荒滩上栖落着大群大群水鸟,翅膀时时拍击那像泥捏似的村落……
我被部队农场分配去养猪。我每天和儿子一起拌猪饲料,烧猪食。那土灶的柴火烧红不透明的早晨,映着我们灰暗的脸。儿子借着灶口闪烁不定的火花,翻看着一本借来的唐诗,他抬起有星云流动的大眼睛说:“爸爸,我和你对诗好吗?你有首诗叫《黄浦江畔》,我想对首《渤海滩头》;你昨天写一首叫《沼泽里的鱼》,我想对首《中枪弹的雁》……”我深深感动:世界上已经没人再读我的诗了,而他却记得。于是,父子俩真的对起诗来。……把每首即兴写的诗,都丢进火里。我俩说:“火焰是我们诗歌唯一的读者”。
喂猪是我们父子流放生涯中最大的乐趣。在没有散尽的寒雾中,把一大桶一大桶热气腾腾的猪食,倒进猪圈,倒进猪槽,看着那些饥饿得要发疯的猪来争食,实在太激奋了。儿子给每头猪取了个名字:“老病号”、“老祖宗”、“八百罗汉”、“饿死鬼”……真的,由于缺粮缺饲料,每头猪都饿得脊骨突露,嘴尖毛长;有的竟相互撕咬,你噬它的耳朵,它啃你的尾巴……
饲料危机是最大的经济危机,我们只有打开猪圈去放牧。几十头毛色不同、性格各异的猪,在海滩边,在潍河旁,咕咕哝哝、呼哧呼哧地咀嚼着野草和没有挖尽的红薯根、萝卜叶……中午,初夏的阳光已经有些温暖,我和儿子就跳进这即将入海的水流里,尽情浸没和扑腾……没有人,只有云和鸟和太阳,还有远远的草地上正在觅食的猪。草有些绿了,更绿了——盛夏来到。赤裸裸、水淋淋的儿子伏在沙滩上晒暖。他的手指伸进砂砾中写诗:“太阳烘着地球,像烤一块面包……”
是的,我们是多么需要一块面包!
几年后,我们被允许回城,回北京——由于林彪在温都尔汗的荒野上爆炸,我们这些被迫害者就有了点儿希望。车轮又把我们全家带回旋转着许多车轮的社会。此时,和猪和海洋、天空一起生活了几年的儿子,已长成真正的英俊少年,他从寂寥、壮阔的生活中,带回几盒在草棵中采集的昆虫标本和两册自写自编的诗集;一册自由体,名《无名的小花》;一册格律体,名《白云梦》。随后,生活就给他上紧了发条。他比时钟更紧张,更匆忙。他去街道服务所里干活,筛石灰、拉大锯、刨树根、刷油漆、爬到楼顶去刮顶棚铁锈、在高温熔炉旁拌糖浆……他狂热地劳动着,好像真正成了枚万能螺丝钉。
一个生日又一个生日,都在恼人的轰响声中过去……他开始看书。正好,我们当年被抄走的书籍,零零散散地发还点,总算有点书了。顾城的狂热于是转了方向,没日没夜地沉浸在越堆越高的书中。他把过去细看过的两大本《辞海》重新扫瞄;他读所有的诗歌、小说、哲学、科学、政治经济学……他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像复印机似的,常常一个通宵就能翻完厚厚的一叠。
他还自学绘画……
他室内的灯光几乎是彻夜不熄的。梦幻,分不清月光和阳光,时时在伴随着他,索绕着他。白昼午睡和黎明欲来没来时,是他写诗的最好时刻。儿子写诗似乎很少伏在桌案上,而是在枕边放个小本、放支圆珠笔,迷迷蒙蒙中幻化出来飞舞出来的形影、景象、演绎、思绪……组合成一个个词汇、一个个语句,他的手便摸着笔,摸着黑(写时常常是不睁眼的)涂记下来。有时,摸到笔摸不到小本本,他就把句子勾划到枕边的墙壁上——他睡的墙头总是涂满了诗,还有许多用漫画笔法画的小人小狗小猪……他那后来传诵一时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睛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就是在这样的迷蒙中,幻化中,受积聚到一定程度的灵感的迸发冲击,涂写到墙上去的——犹如云层激发出雷电……
顾城开始了他的投稿生涯。在这方面他好像也有点朦胧。他并不研究每个刊物的用稿标准,只是把那些大大小小刊物的名字事先写好信封,一大叠,用的时候,就把诗稿自上而下顺序一装,碰到谁就是谁,从《人民文学》到县办刊物,一律平等。
我们家的门常被敲响了,一些青年带来了他们的崇敬与争论。顾城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地同他们讨论他的《远和近》、《弧线》等等;最后实在应接不暇,便写文给报刊集中解说。那个时候,“朦胧”是让人难解又兴奋的事,我们家也常常争论探讨。奇怪的是,我那不朦胧的诗却从来不引起争论,总是在报刊较为舒适的位置上安憩。
关于顾城诗的争论时起时伏,最后渐渐平息下来。顾城在南方过了一年,接着结婚,然后回北京过了一段比较平静的日子。他睡醒来便去种丝瓜、扁豆,有时去讲课。他越来越能讲,也越来越沉默。我俩常常应邀去各个院校讲课,我讲过去的事,他也讲过去的事。我讲的是战争、烽火、布满尸体的山谷、哭泣的村庄;他讲的却是文化大革命,那些寂寞危险的日子,他所爱的鸟,他所梦想的人和各种昆虫的故事……
他总是看着远处讲话,说他要在山上筑一座小城,安一门金属的大炮,养一些兔子,“我是一个王子/心是我的王国……”“蓝海洋在四周微笑/欣赏着暴雨的舞蹈……”所有听的人都很安静,被他带进了一个童话世界,只有他一个人还在向前走着,好像在继续他儿时未完成的游戏……
后来他真的走了。1987年去德国参加明斯特国际诗歌节,又去了英国、法国、美国、瑞典……走进一个个诗歌的盛会,推开一所所大学的门扇(我怎么也不明白,他这个小学生是怎么变成一个大学研究员的)。他在那些国家的课堂里、讲台上,依旧穿着浅灰色的中山服,眼睛向远处看着,讲中国古老的文学和哲学,还有最新的诗……
--------------------------------------------------------------------------------
李心艾饰演李长乐,李未央的大姐,京城第一美人,父亲是当朝尚书,母亲是世家之女,显赫的家世纵出她自负自傲、自私冷酷的性格,认为天下间没有女人能胜过自己,可就在这时,李未央出现了,明明处处不如自己,却能得到拓跋浚的另眼相看,这让李长乐产生了危机感,一心想要这个隐隐有超越之势的妹妹自眼前消失;
个人简历:
李心艾;
外文名:Hsin Ai Lee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汉族
星座:白羊座
血型:B型
出生地:陕西西安
出生日期:1990年4月10日
职业:演员、歌手
经纪公司:创映**公司
代表作品:天台爱情、班淑传奇
演艺经历:
李心艾2013年出演《天台爱情》女主角并演唱**插曲《快门慢舞》正式进入娱乐圈;2014年出演于正工作室出品的古装剧《班淑传奇》出演其中角色寇兰芝;7月份再次出演于正工作室出品的古装单元剧《美人制造》;饰演第四篇《不老传说》中的诸葛小仙;同年还出演**《张震讲故事》;2015年2月拍摄何炅导演的**作品《栀子花开》饰演高美雪一角;4月拍摄邹集城导演的电视剧作品《花火》;2016年出演电视剧《锦绣未央》在剧中饰演第一美人李长乐;
剧情简介:
南北朝期间,群雄逐鹿,烽烟四起,战事纷争不断。出身北凉王族的少女心儿,本是天真善良的无忧公主,过着万人宠爱、恣意随性的快乐日子。然因北魏元帅为抢战功,欺君罔上擅自出兵,导致北凉上下一夜之间血流成河,天之骄女被迫流落异乡。北魏尚书府遗弃在乡下的庶女李未央意外救了心儿,后又因掩护心儿被追兵杀害。心儿不得不以李未央之名,勇敢地活下去,一个人背负起两个女孩的命运与苦难。回到太傅府,化名李未央的心儿不仅要与仇敌叱云氏一族斗智斗勇,还意外卷入与北魏皇子的情仇纠葛。苦难与坎坷没有将心儿打倒,反而赋予心儿无上的智慧与心胸,心儿历尽艰险磨难,终为父系一族正名,同时也收获了曲折感人的美好爱情。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品搜搜测评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