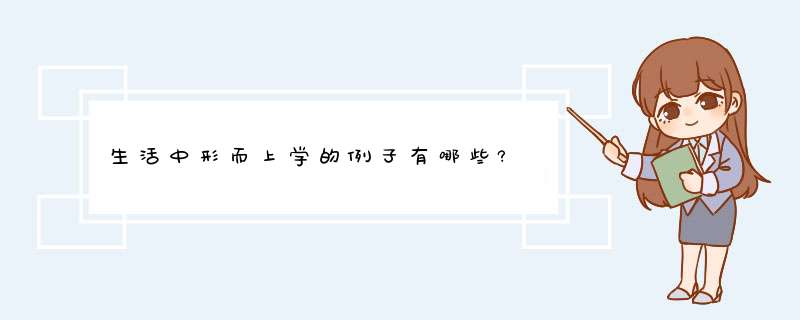
例如:自然诗人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按照一定尺度生成,一定尺度燃烧,永不熄灭。
形而上学是原始哲学的一个门类,指对在无法用经验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对世界本质的猜测。它最初是研究存在的本体论体系,其理论原则是柏拉图的世界二重化。 13世纪起被作为哲学名词,用以指研究超经验的东西(灵魂、意志自由等)的学问。
以下是形而上学探索的问题的相关介绍:
形而上学探究宇宙万物根本原理的那一部分,它关注的问题有: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宇宙万物的生成和演化,时间和空间的本质,自然界的规律法则,灵魂是否存在,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自由意志等。总之,存在,虚无,宇宙,灵魂,自由意志,都属于古老的形而上学话题之一。
新的问题不断进入形而上学的研究范围,目前还没有够列出形而上学的问题统一起来的共同特征来定义“形而上学”,只是列出当代被认为是形而上学的哲学问题。
以上资料参考——形而上学
塞萨尔・巴列霍(1892―1938)是西班牙语诗坛上最伟大也是最复杂的诗人之一。说他伟大,是因为他的诗歌创作是整个西班牙语先锋派诗歌的里程碑说他复杂,是因为他的作品比贡戈拉夸饰主义的巴洛克更难理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标新立异的西班牙语先锋派诗坛上,他依然是一位标新立异的诗人。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如此复杂、如此难懂的巴列霍竟然又是西班牙语世界一位传播十分广泛的诗人。这或许正是他的伟大之处,雅俗共赏历来是衡量伟大作家和艺术家的标准之一。
巴列霍于1892年3月16日出生在秘鲁北部安第斯山区的圣地亚哥・德・丘科镇。其故居座落在卡哈班巴区的哥伦布街96号,如今这条街已更名为塞萨尔・巴列霍街。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西班牙籍牧师,但在他母系亲属中有印第安人血统。在11个兄弟姐妹中,他是最小的一个。他受洗礼时的名字是塞萨尔。亚伯拉罕。在他的童年时代,家境虽说不上富有,但也不算贫穷,他的父亲曾当过家乡的镇长。但是要培养他上大学,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1910和1911连续两年,他曾先后在特鲁希略大学和利马的圣马可大学注册,都因经济困难而退学。他于1913年入特鲁希略大学文哲系,两年后又同时在法律系注册。从那时起,他一直半工半读,主要是在小学任教:秘鲁著名的土著小说作家西罗・阿莱格里亚就曾是他的学生。
巴列霍于1918年来到利马,在圣马可大学文学系注册。作为出身卑微的“混血儿”,巴列霍立即感受到了大都市的世态炎凉,但又很快找到了良师益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结识了具有民族气节和正义感的作家与诗人贡萨雷斯・普拉达、埃古伦、马里亚特吉等人,并与后者一起创办杂志《我们的时代》。这一年他完成了第一部诗集《黑色的使者》,并于第二年出版,尽管书上署的仍是1918年的日期。诗集在报刊上受到了好评。
1920年,他回到家乡特鲁希略。在社会动乱中,因“鼓惑青年、煽动闹事”的罪名,在铁窗下度过了112天。只是迫于知识界和大学生们的强大压力,地方当局才于1921年暂时释放了他。这段经历对巴列霍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常在他此后的作品中折射出来。就是在这一年,他完成了《特里尔塞》的创作,并有一部短篇小说(《在生与死的背后》)获奖。1922年,他出版了诗集《特里尔塞》。1923年,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音阶》和中篇诗化小说《野蛮的寓言》。当时有传言说,他的案子可能要重新开庭,他便于6月17曰乘船赴欧洲,7月13日抵达法国。从此,他再也没回到自己的祖国。
在巴黎,他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好,并且要与疾病抗争。1926年,他与胡安・拉雷塔共同创办了《繁荣・巴黎・诗歌》杂志。欧美的先锋派诗人赫拉尔多・迭戈、特里斯坦・查拉、维森特・维多夫罗、胡安・格里斯、皮耶尔・勒韦尔迪、巴勃罗・聂鲁达等都曾为他们撰稿。1927年,他经受了深刻的精神与道德危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8和1929年他两度赴苏联访问。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大量的报刊文章,并创作了中篇小说《钨矿》(1931)。1930年,他在马德里的《玻利瓦尔》杂志上发表访苏观感,并在西班牙结识了阿尔贝蒂和萨利纳斯等诗人。回到巴黎后,他的政治活动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并于年底将他驱逐出法国。他只好重返西班牙。在那里,他出版了中篇小说《钨矿》、通讯报导《俄罗斯在1931》和《克里姆林宫前的思考》。同年,他加入了西班牙***,并第三次访问苏联。
1932年他又回到巴黎,在贫病交加中从事政治活动与文学创作。1936年爆发的西班牙内战激发了他高度的政治热情,他积极参与筹建“保卫西班牙共和国委员会”,参加群众集会和声援共和国的活动,赴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做宣传报道。1937年,他作为“第二届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的秘鲁代表再赴西班牙,并曾亲临马德里前线。在此期间,他创作了《疲劳的岩石》和《西班牙,请拿开这圣杯》以及《人类的诗篇》中的诗作。1938年,他开始重建“秘鲁保障与自由运动”。由于过度疲劳,健康恶化,于4月15日在法国巴黎去世。1939年,人们出版了他的诗集《西班牙,请拿开这圣杯》和《人类的诗篇》。1970年人们将他的遗体移到有名的帕尔纳斯山公墓(Montparnasse)o
巴列霍的一生,是充满痛苦的一生,也是不懈追求的一生。他的痛苦不仅是个人的,更是人类的。他的追求不仅是政治的,更是艺术的。综观他的一生,可以说,痛苦始终伴随着他,追求也始终激励着他。对他有了这样的了解,再来分析他的诗歌,就是再难也不会有太大的偏颇。
巴列霍从1908年(16岁)开始写诗,至1918年完成了《黑色的使者》。在这十年中,他明显地接受了现代主义诗人卢文・达里奥、埃雷拉・伊・雷西格和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的影响。但《黑色的使者》却是一部从现代主义诗歌中脱胎出来的全新的诗集。它与现代主义诗歌的根本区别在于:现代主义是脱离现实的,既脱离社会现实,也脱离诗人所处的氛围与心境,而《黑色的使者》却具有鲜明的自传成分,诗人表达的是自己的经历、观念、信仰、价值观和赤裸裸的人性:现代主义诗人追求异国情调,具有明显的世界主义倾向,而巴列霍的作品却恰恰相反,具有地方的、民族的、本土主义的特征;现代主义诗人所追求的是语言的典雅与韵律的和谐,而巴列霍不仅常常将日常的口语镶嵌在字里行间,有时还会将语言支解或根本不遵循现有的语言规范。
巴列霍的第一部诗集《黑色的使者》是由《精巧的檐板》、《潜水员》、《土地》、《帝王的怀念》、《雷声》和《家庭的歌》组成的。《黑色的使者》是作为全书的序诗出现的。它表现了诗人在生活打击面前的怀疑和失望:
生活中有如此厉害的打击……我不知道!
就像是上帝的仇恨;面对它们
似乎一切苦恼的后遗症
都沉积在灵魂……我不知道!
打击虽然不多;然而……能在最冷酷的面孔
和最结实的脊背上开出阴暗的沟壑。
它们或许是野蛮的匈奴人的战马
要么就是死神派来的黑色使者。
诗集中有一组回忆古老印加帝国的诗篇,题为《帝王的怀念》,这是本土主义在巴列霍诗歌中的集中表现。在第三首中,他这样写道:
耕牛走在通往特鲁希略的路上
像古老的酋长,沉思冥想……
对着生铁般的暮色,
像为失去领地而哭泣的国王。我站立在城头,思考着福祸交替的规律;在耕牛寡妇般的眼神里无时不在的梦想已经腐烂下去。
在这首诗里,诗人的本土主义不仅表现在对古老印加王国的怀念,还表现在对克丘亚语的自然运用,这样就给诗作增添了印第安民族特有的韵味与情调。诗人在这部诗集里抒发了对亲人和故乡既浓烈又苦涩的情怀。比如,他无可奈何地看着父母衰 老下去,看着他们如何走到人生的尽头:
父亲变得衰弱无力
就像是一个除夕,
心不在焉地回首往事的
琐碎、启迪和残迹。
这样的诗句暗示着在78岁高龄的父亲心中,往事都混杂在一起了。对他来说,生活目的不过是未来子孙的繁衍,而“未来”他是再也看不到了。远离家乡的诗人对父母充满了怀念之情:
父亲在沉睡。威严的面孔
表明平静的心灵。
此时此刻他多么甜蜜……
如果他有什么苦涩――那就是我。
家中一片沉寂;人们在祈祷:
今天没有孩子们的消息。
父亲醒来,聆听逃往埃及
那依依惜别的话语。
此时此刻他多么近啊……
如果他有什么遥不可测~一那就是我。
父亲在沉睡。威严的面孔
表明了平静的心灵;
现在他多么甜蜜……
如果他有什么苦涩――那就是我。母亲漫步在果园里,嗅着已经不存在的气息。现在她是那么温柔,那么出神、爱抚、飘逸。家中一片沉寂,没有喧闹,没有消息,没有天真,没有稚气。如果有什么波折在傍晚降临并瑟瑟有声,那就是两条白色的古道,弯弯曲曲。我的心正沿着它们走去。
在这组诗中,巴列霍还写了一首怀念兄长米格尔的作品:
哥哥,今天我坐在家中的石凳上,
你使我们感到无比凄凉,
记得此时此刻咱们正在玩耍,
“可是,孩子们……”
母亲抚摸在我们身上。
米格尔,八月的一个夜晚,
破晓时你去躲藏;
可这一回你没有欢笑,只有悲伤。
“躲藏”既指儿时的游戏,又指兄长的去世。对于弟弟的童心来说,哥哥没有死,不过是“藏了起来”,诗人以此将对哥哥的怀念与对孩提时代的回忆揉在了一起。
诗集中有一些情诗,其中一首十四行诗题为《逝去的恋歌》:
此时此刻,我温柔的安第斯山姑娘丽达
宛似水仙花和灯笼果,你在做什么
君士坦丁堡令我窒息,
血液在昏睡,像我心中劣质的白兰地。
此时此刻,她的双手会在何方
它们在将傍晚降临的洁白熨烫,
正在降落的雨
令我失去生的乐趣。
她那蓝丝绒的裙子将会怎样
还有她的勤劳,她的步履
她那当地五月里甘蔗的芳香
她会在门口将一朵云彩眺望,
最后会颤抖着说:“天啊,真冷!”
一只野乌在瓦楞上哭泣忧伤。
曾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秘鲁圣马可大学教授阿尔瓦罗・门多萨先生对笔者说过,他对此诗做了考证:印第安姑娘丽达是诗人家中的女仆,她总是翘首盼望在外飘泊的年轻男主人的归来。对诗人而言,尽管这段经历已成过去,但他的怀念之情却依然婉约动人,这样的诗歌在巴列霍的作品中是不多见的。
《特里尔塞》是巴列霍于1919至1922年间在利马写成的,1922年出版。它与同一年出版的《尤利西斯》(乔伊斯)和《荒原》(艾略特)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它在首次出版后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1 931年何塞・贝尔加敏在西班牙为该书作序并再次出版时才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是一部与现代主义传统彻底决裂的作品,是拉丁美洲先锋派诗歌的里程碑。它打破了传统的诗歌技巧,表现了诗人大胆的开拓精神。
首先,诗集的名字就令人难解,“特里尔塞”(Trilce)是诗人杜撰的新词,Tri与3相关,它体现了诗人对事物除同一性、二重性以外的第三极思考。整个诗集以人的孤独、无助为基调,表现在非正义的社会中,人类所遭受的重重苦难。书中的诗没有标题,只有罗马数字。在这些诗句的迷宫中,读者没有任何向导,同时也就没有任何约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这部诗集中,有许多用数字、日期、地点和科学名词组成的诗句,作为语言结构,有时简直是无法理解的,有时只是靠词素的声音来表达特定的情感和意境。其中数字尤其重要,这是因为巴列霍赋予了它们特殊的内容,而它们本身的意义已不复存在。比如:按照传统的观念,“一”是完整的象征,而对巴列霍来说,却意味着孤独;“二”象征着男性和女性“结合”,而对巴列霍来说,则代表着无目的的辩证法;“三”是圣三位一体和完美的象征,而对巴列霍来说,则象征着毫无意义的传宗接代;“四”本来代表着土、气、水、火四大元素,而对巴列霍来说,却代表着牢房的四堵墙。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从内容上讲,《特里尔塞》与《黑色的使者》是一脉相承的:真诚地揭露社会的黑暗与人类的苦难。对巴列霍而言,人生就是一个悲剧。诗人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无不是人类的痛苦。从形式上讲,《特里尔塞》既背叛了西班牙语诗歌的传统,也脱离了先锋派诗歌的主流。他非常注重诗歌的直观形象,而不是通过人的理智来进行情感的交流。在第XXxVf首诗中,他这样写道:你们,请不要立足于和谐双倍的稳定,请断然地拒绝对称。请你们干预尖端相互争夺的冲突在最激烈的交锋中跳跃着穿过针孔!
这样的诗句虽颇为晦涩,但却不难看出,巴列霍拒绝廉价的稳定,情愿通过不和谐的复杂途径去冒险。他主张鼓励人们拒绝对称,通过语言的矛盾和冲突来揭示自己的内心世界。总之,《特里尔塞》不仅突破了古典诗歌的传统,也突破了西班牙语的语言结构和思维逻辑。
在探索诗歌的形式方面,《特里尔塞》的确是一个大胆的突破。诗集中许多类似梦呓的诗句把立体主义、创造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诸多流派融合来,但又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流派。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标新立异。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以一种荒谬的语言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和人类的痛苦与不幸。当巴列霍抒发自己的孤独和苦闷时,当他描写自己在狱中的遭遇和抗议社会不公正时,当他回忆自己失去母亲和家庭温暖时,诗人流露出了对所有被压迫者的关爱与同情。正是这种对人的终极关怀使巴列霍在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两次来到反法西斯前线,写下了《西班牙,请拿开这圣杯》。诗集的名字取自《圣经》中的《马太福音》,《圣经》中的译文是这样的:他(耶稣)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亦有此话,译文大同小异)。《圣经》中的“杯”指的是耶稣即将遭受的苦难,而巴列霍所说的“杯”显然是指西班牙人民遭受的苦难。本来,有人将这个诗集译为《西班牙,我饮不下这杯苦酒》,就汉语而言,或许更加明白易懂,但却很难使人与《圣经》联系起来,所以在此没有沿用已有的译法。在《圣经》中是耶稣向上帝祈求,而在这里是诗人向西班牙祈求。由此可知,对巴列霍来说,西班牙革命的共和国就是他的理想之所在。这部诗集由15首诗组成,其内容和形式虽没有《特里尔塞》那么惊世骇俗,但依然保持着巴列霍的风格,与其它同一题材的诗歌迥然不同。这时的巴列霍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诗中已经将工人看作“救星”: 工人,我们的救星,我们的救世主。
兄弟,请原谅我们欠下的债务!
值得注意的是,巴列霍虽然已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在这部诗集中却不时影射《圣经》中的情节。这样可能会使天主教国家的读者感到亲切。如其中的第8首《群众》与拉撒路复活的情节就有些类似:
战斗结束,
战士死去,一个人向他走来
并对他说:“你不能死,我多么爱你!”
但尸体,咳!依然是尸体。
于是,大地上所有的人
包围着他;伤心而又激动的尸体看见他们;
他慢慢地欠起身,
拥抱了第一个人;开始行进……
《人类的诗篇》是巴列霍在1923年以后写的作品,是他的遗孀和劳尔・波拉斯・巴雷内切亚一道于他死后(1939)在巴黎出版的。全书由76首诗组成。不同版本的排列顺序有些出入,个别的诗句也不完全相同。这是一些令人惊心动魄的诗篇,是光怪陆离的诗篇,也是最具有个性和激情的诗篇。1922年以后,巴列霍割断了与家庭和祖国的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拮据、疾病的折磨、世道的不公使他的苦闷与日俱增,他甚至感到个人的总和不能构成一个社会,个人的存在与否是无关紧要的,于是写下了这样的诗篇:
对于猫,谁不以猫相称
唉,我出生了,只不过出生!
谁不叫卡洛斯或其它姓名
唉,我出生了,只不过出生!
无动于衷的个人组成了群众,然而这个群众并不能抹去孤独的感觉。在《特里尔塞》中,诗歌的意境往往是主观的,巴列霍本人就是悲剧的中心,他力图以一种荒谬的语言和时间、生长、永恒、死亡等抽象概念搏斗。但是在《人类的诗篇》中,巴列霍已成了人类的代言人。在这些作品里,他和其他的个人都变小了,甚至转化成一些习俗、服装和疾病,他们惟一的能力就是繁衍后代,这是何等荒谬的现实。在题为《帽子、大衣、手套》的诗中,他写道:
面对法兰西剧院,摄政者咖啡馆,
一张桌子,一把安乐椅
安置在一个隐蔽的房间。
我一走进,扬起了静止的尘烟。
在我橡胶似的双唇之间,
一支点燃的烟,迷漫中可见
两股浓烟,咖啡馆的胸膛
和胸中忧伤的锈迹斑斑。
重要的是秋季移植在秋季中间
重要的是秋季用嫩芽来装点,
皱纹用颧骨,云彩用流年。
重要的是狂噢,为了寻求
冰雪多么炽热,乌龟多么神速,
“怎样”多么简单,“何时”多么急促!
在这首短短的十四行诗中,巴列霍将咖啡馆的“内室”变成”胸膛”,从它的凄凉景象写到诗人的忧伤,然后又写到外部的生活环境和违反常规的荒唐的追求,从而表现了诗人苦闷、失望的心情。这首诗语言浅显,寓意深邃,既令人费解,又耐人寻味。这正是巴列霍作品的特征。
在巴列霍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正处在经济萧条和社会危机之中。他所看到的不是世界发展的前途,而是人类不幸的加剧。在创作《人类的诗篇》时,他已经不是狂热追求诗歌“绝对自由”的青年,已经亲身经历了人类所受的重重苦难。尽管如此,他并没有绝望,始终在号召人们与非正义的社会进行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诗篇》与《西班牙,请拿开这圣杯》是相辅相成的作品。他的革命思想和斗争精神在中篇小说《钨矿》(1931)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部作品中,他强烈地谴责了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对秘鲁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并号召人民进行反抗。值得注意的是,在艺术风格上,他的诗歌与小说是完全不同的。在《特里尔塞》和《人类的诗篇》中,巴列霍没有直接阐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目的,而是通过忧伤的情调、神秘的意境、讽刺的口吻和荒诞的语言,将恶梦般的、支离破碎的现实焊接起来,不过焊接的目的却正是为了将它打碎。
总之,从诗歌内容上说,巴列霍是一位革命的诗人,而从诗歌的艺术形式上看,巴列霍是一位勇于创新的诗人。他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品搜搜测评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